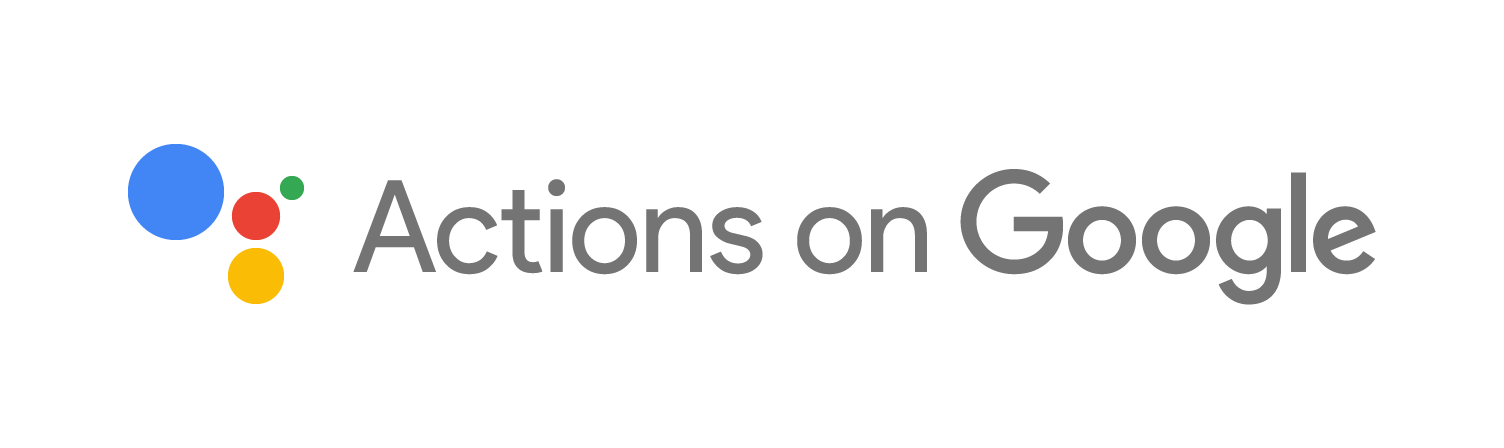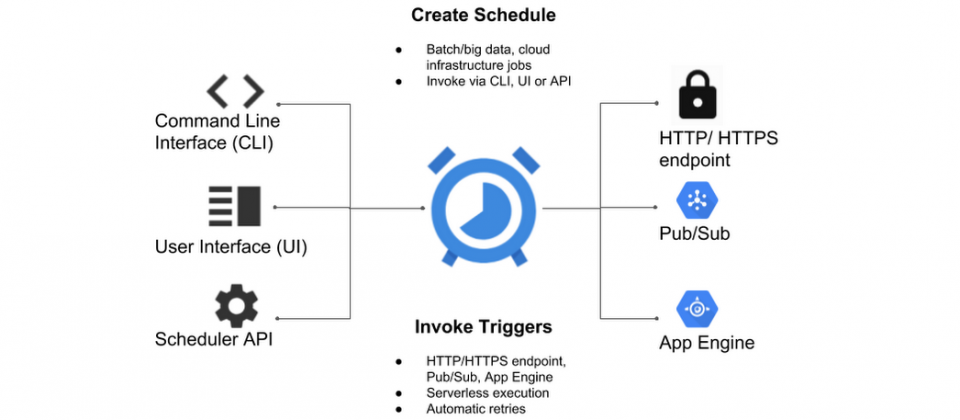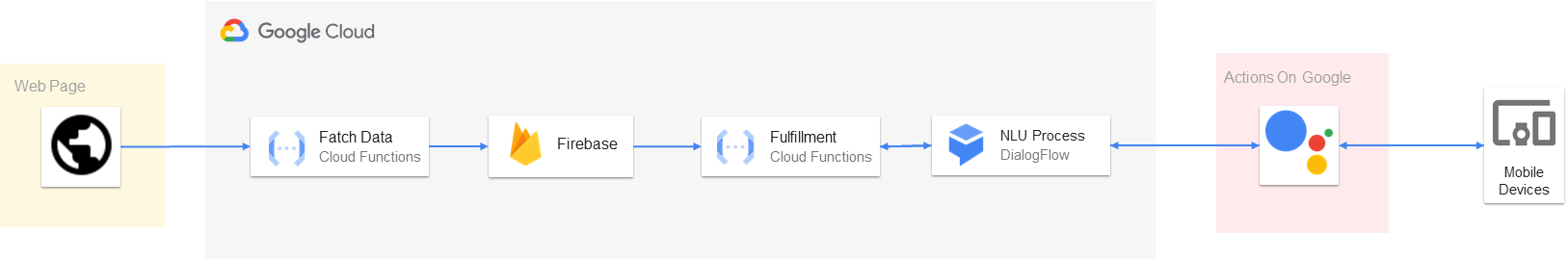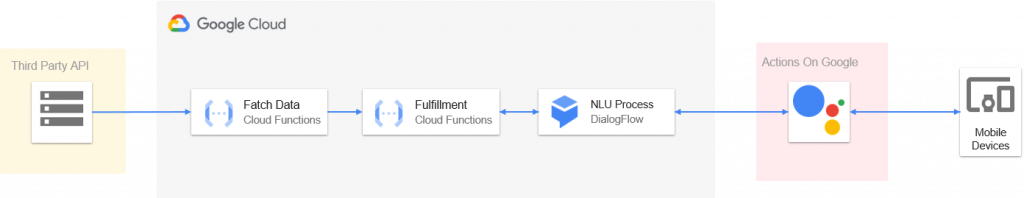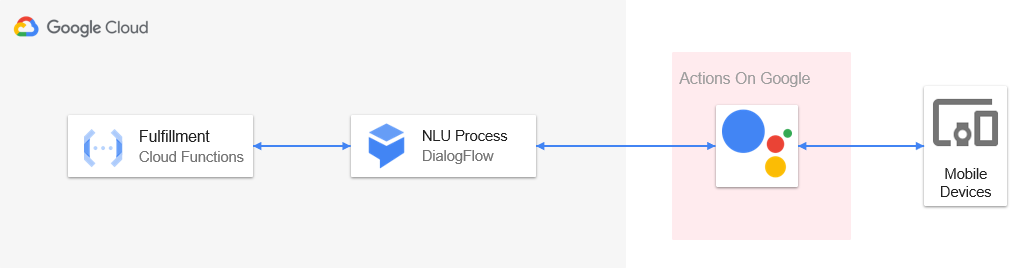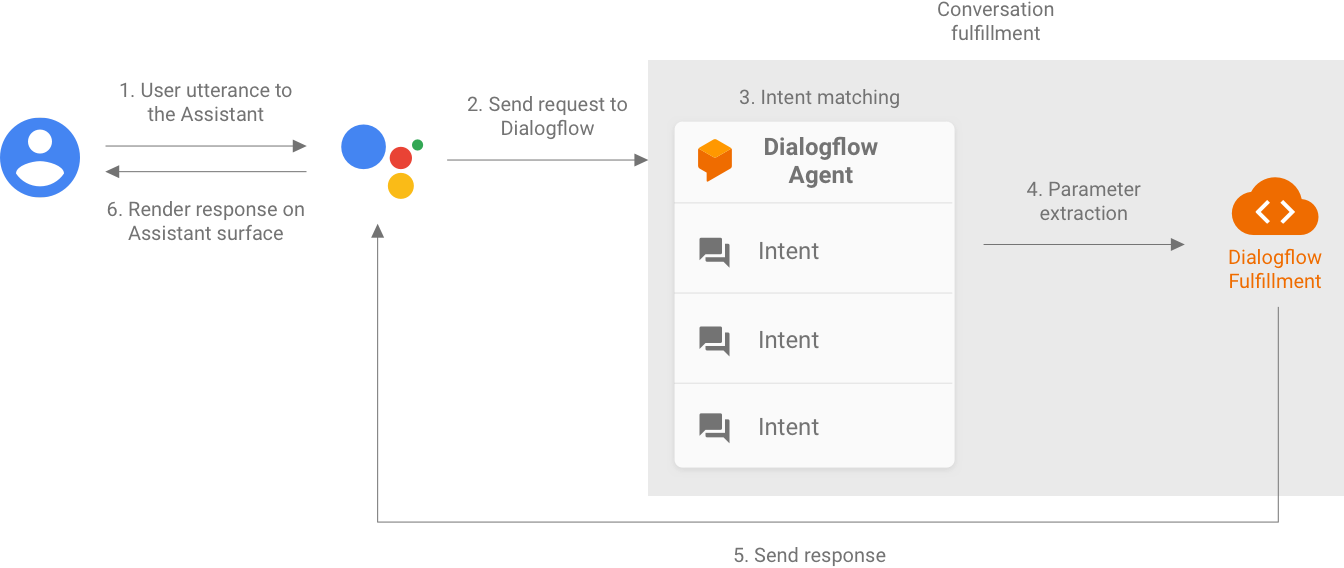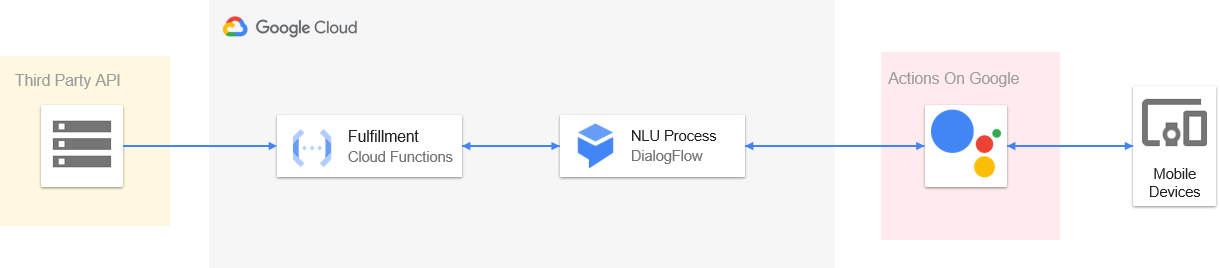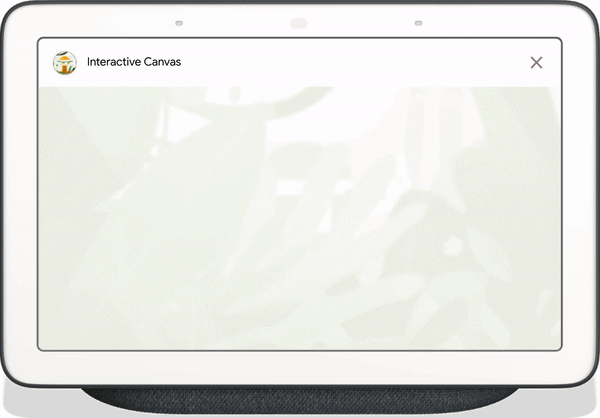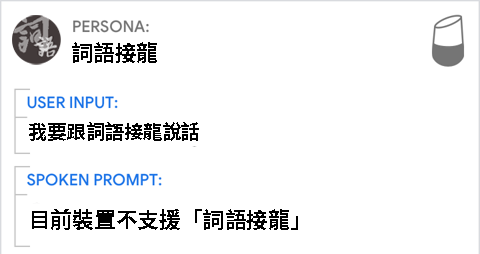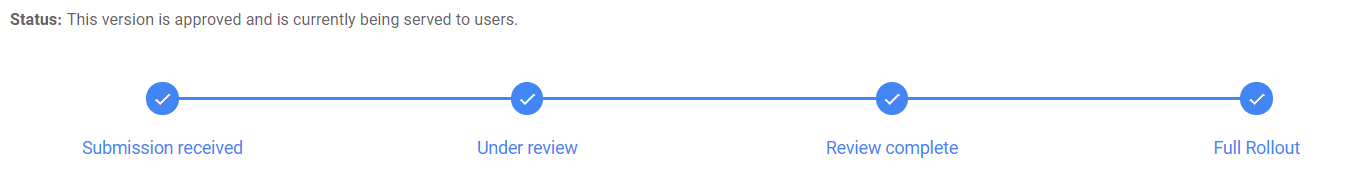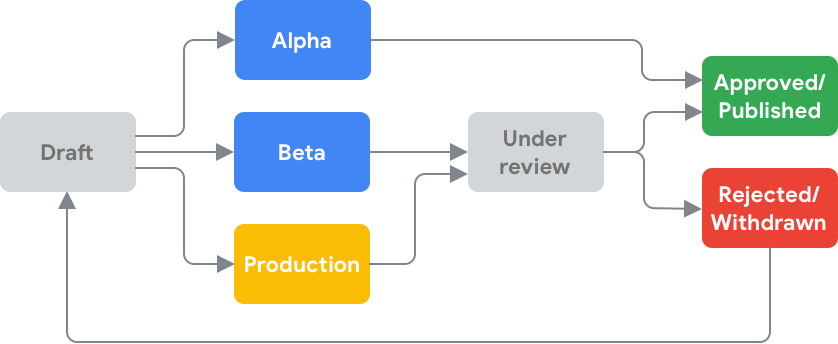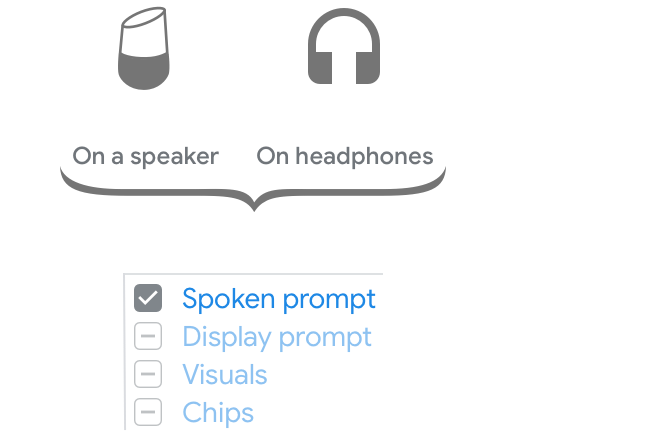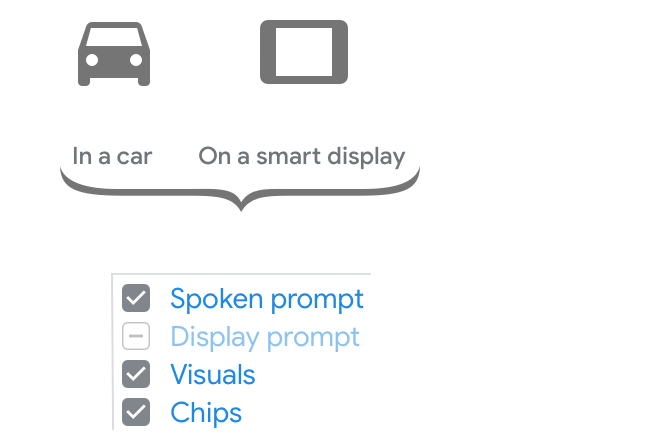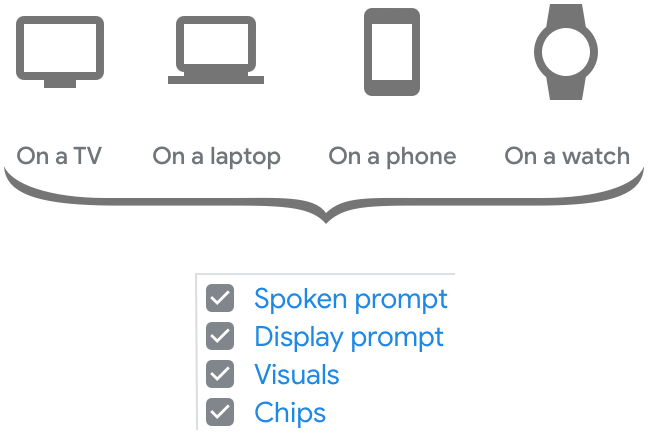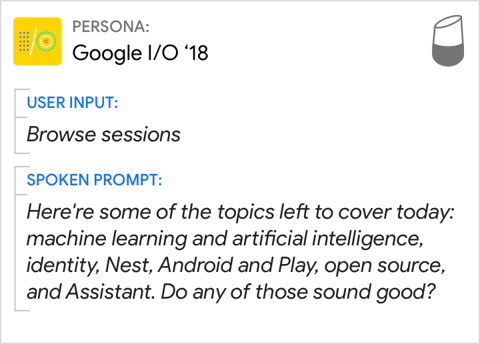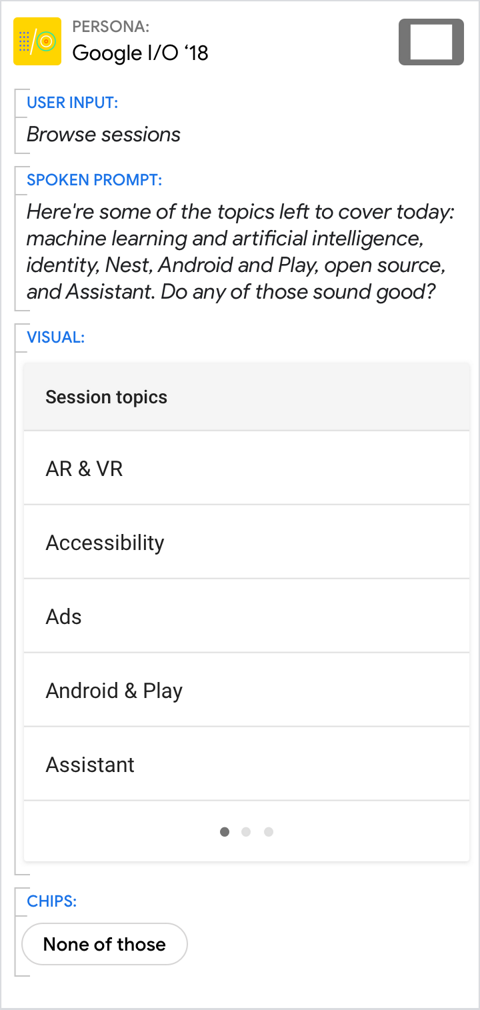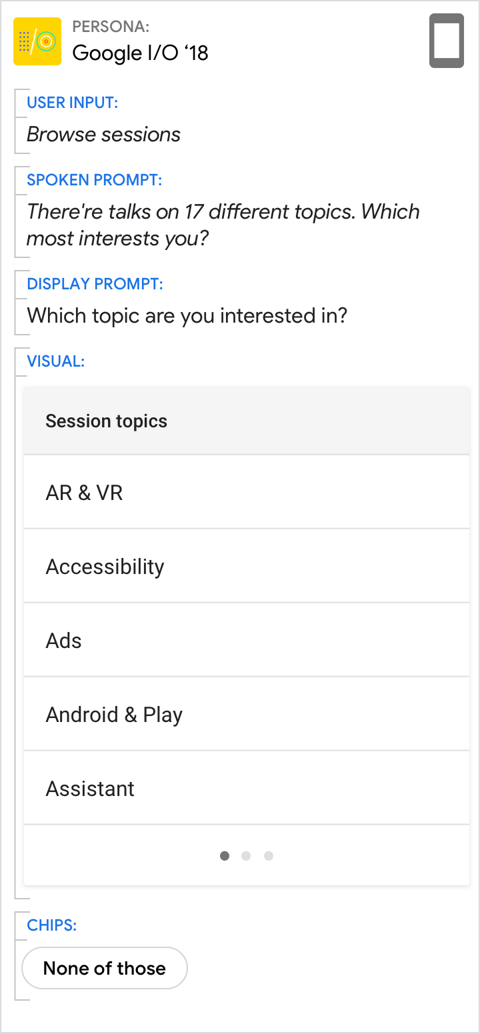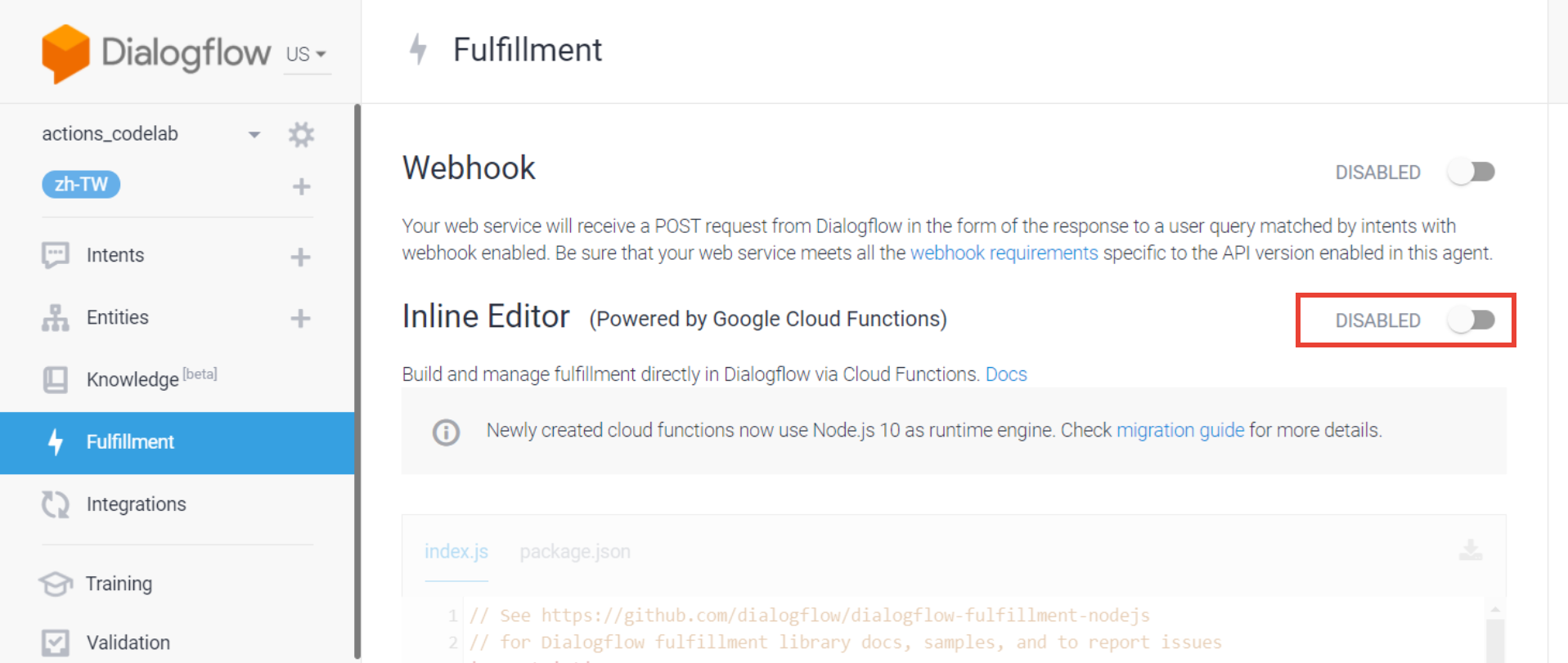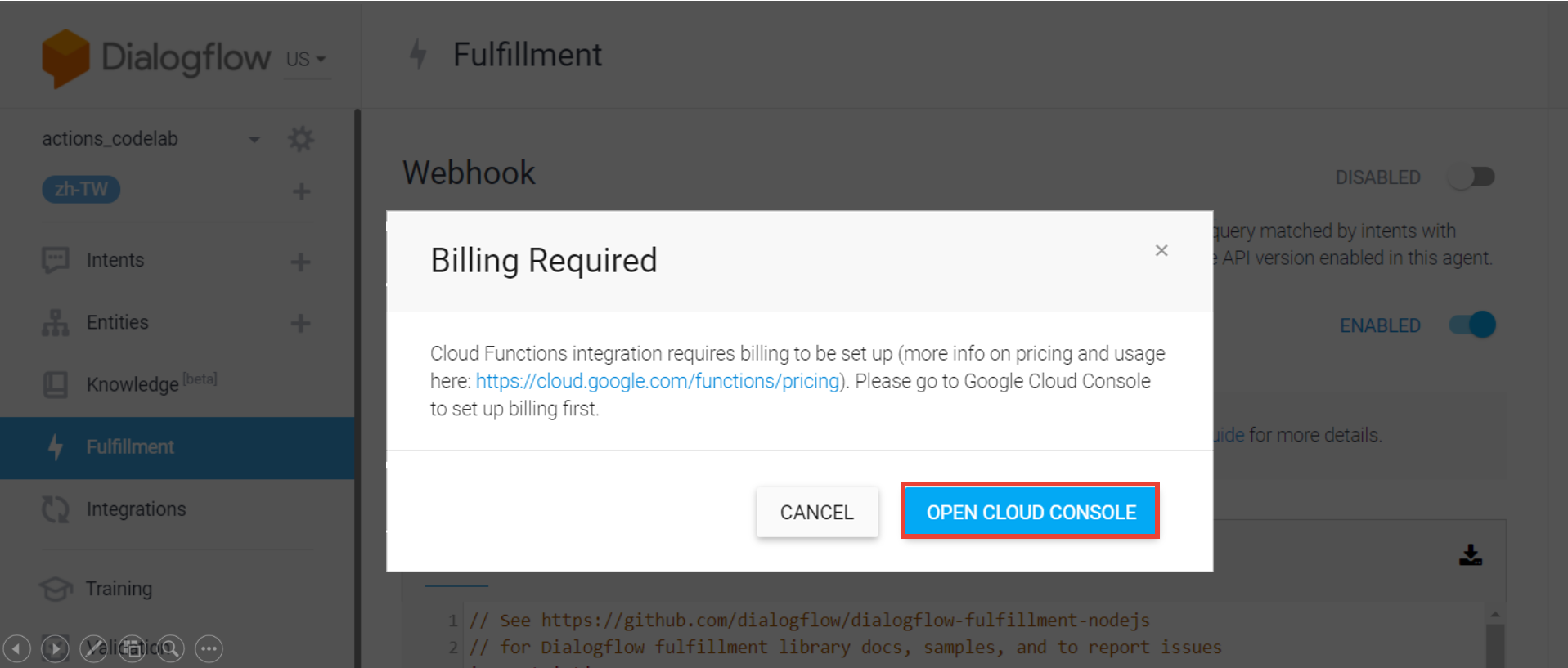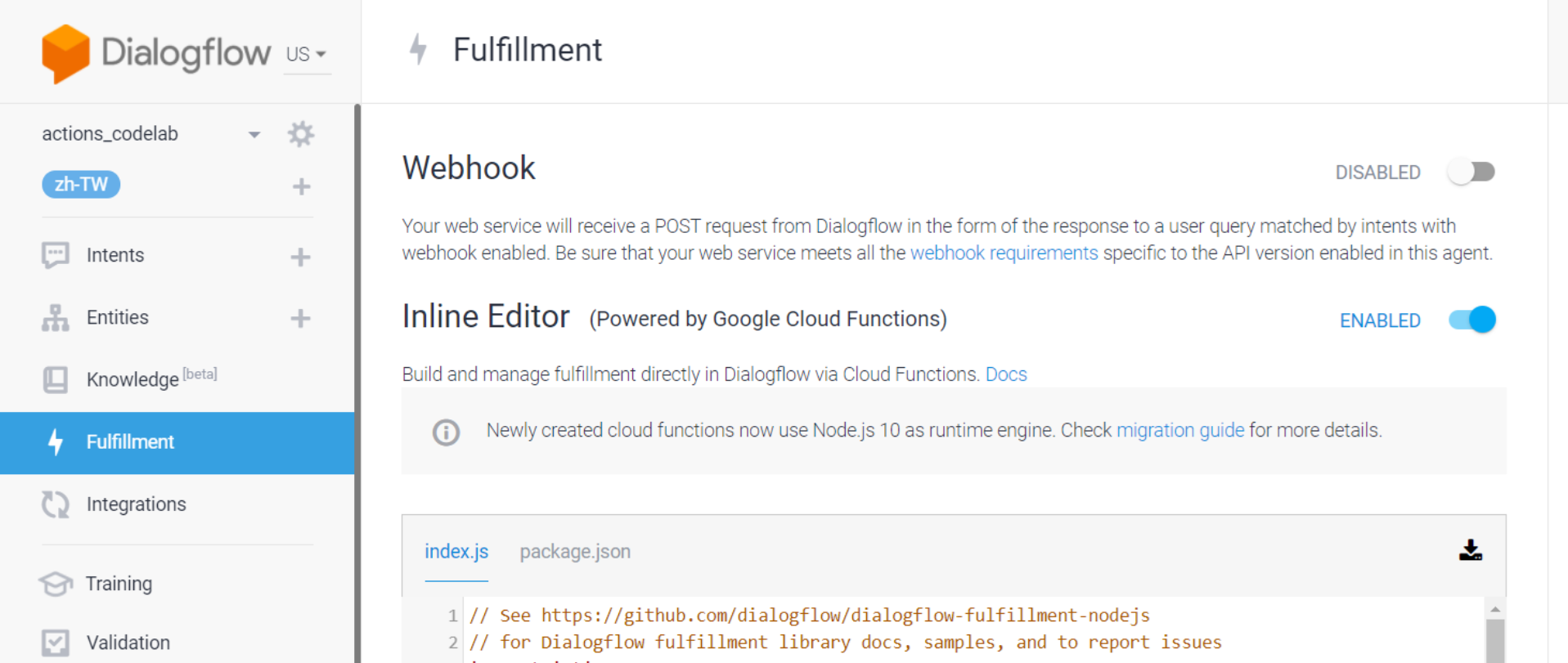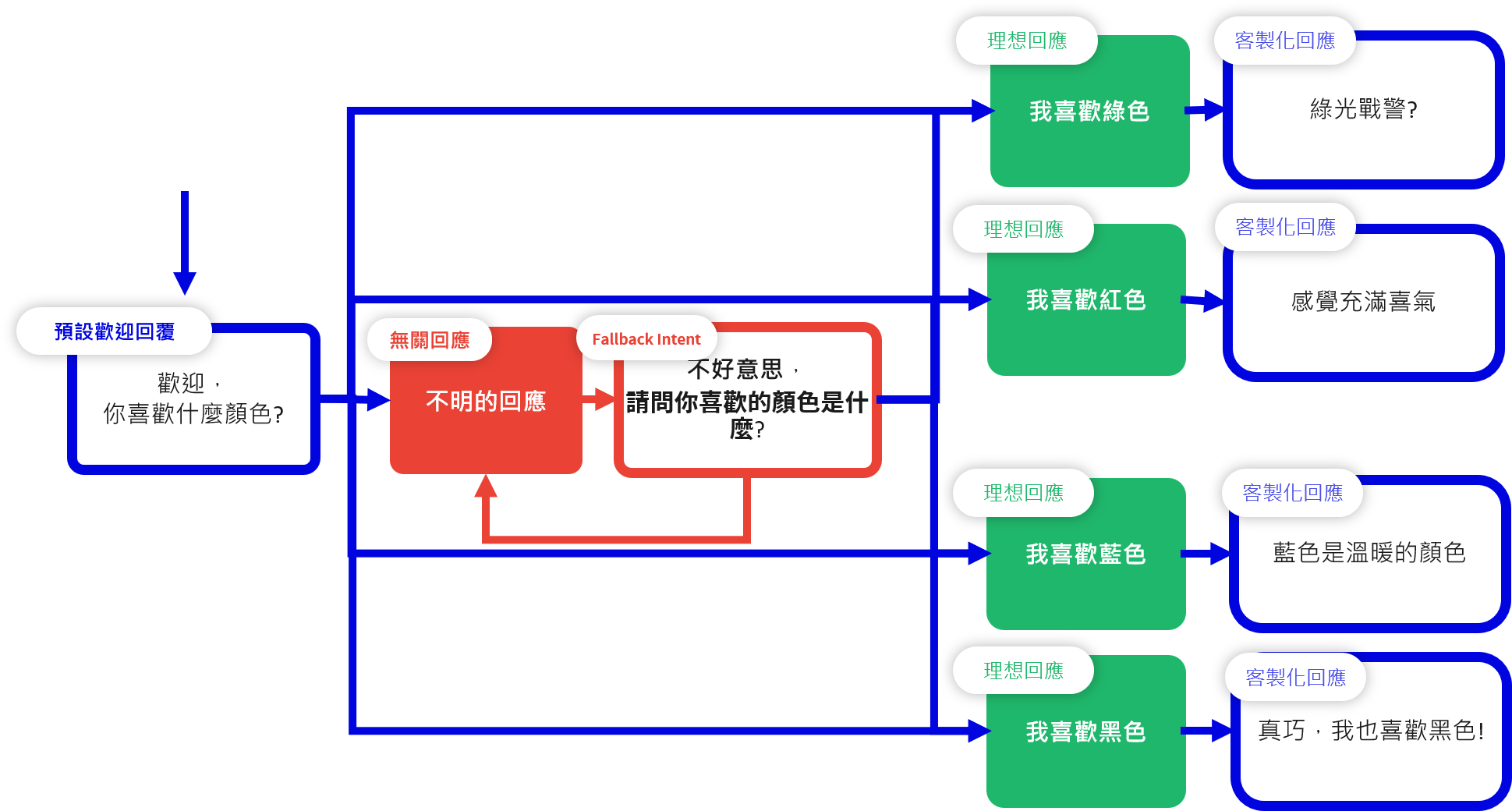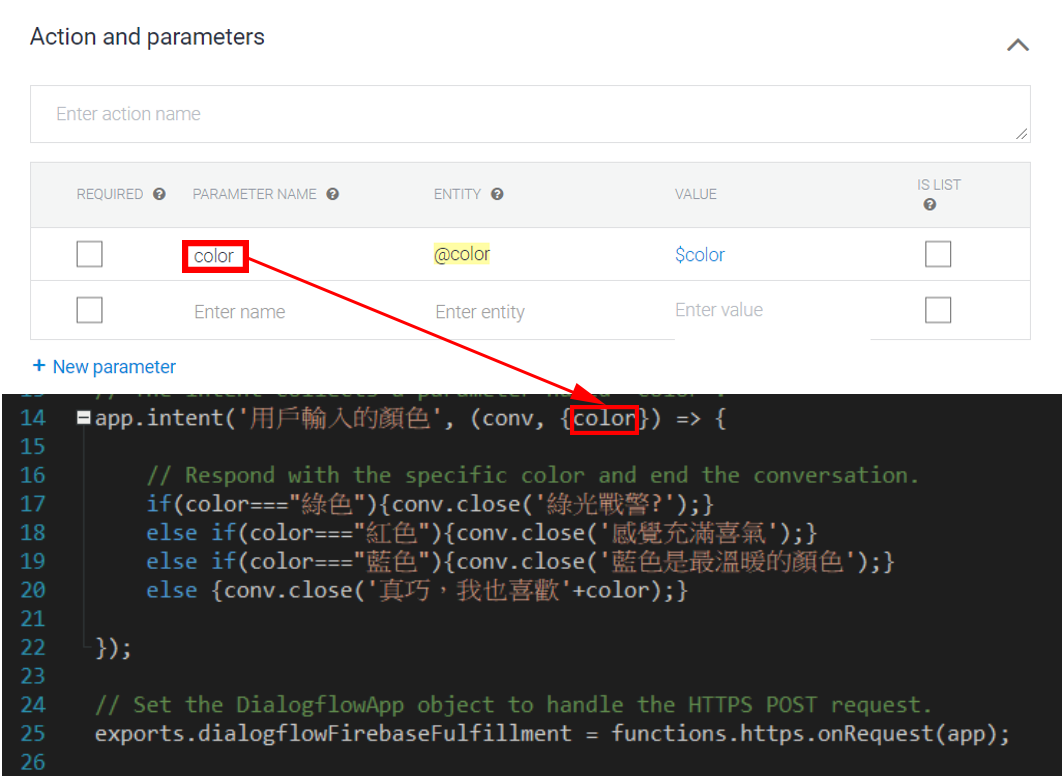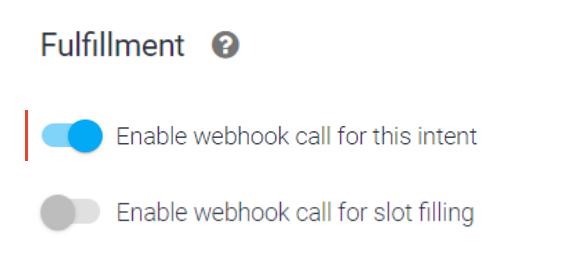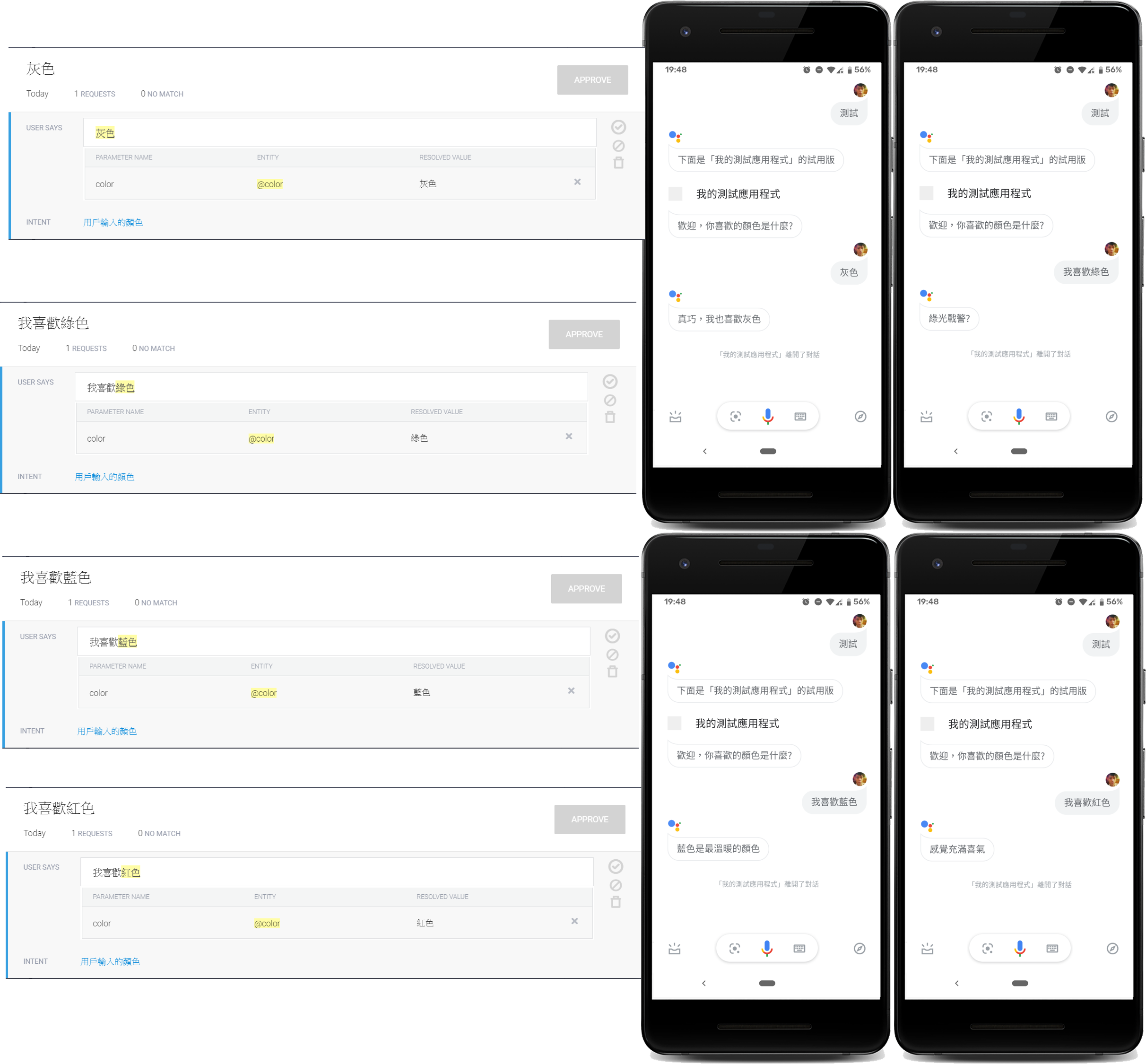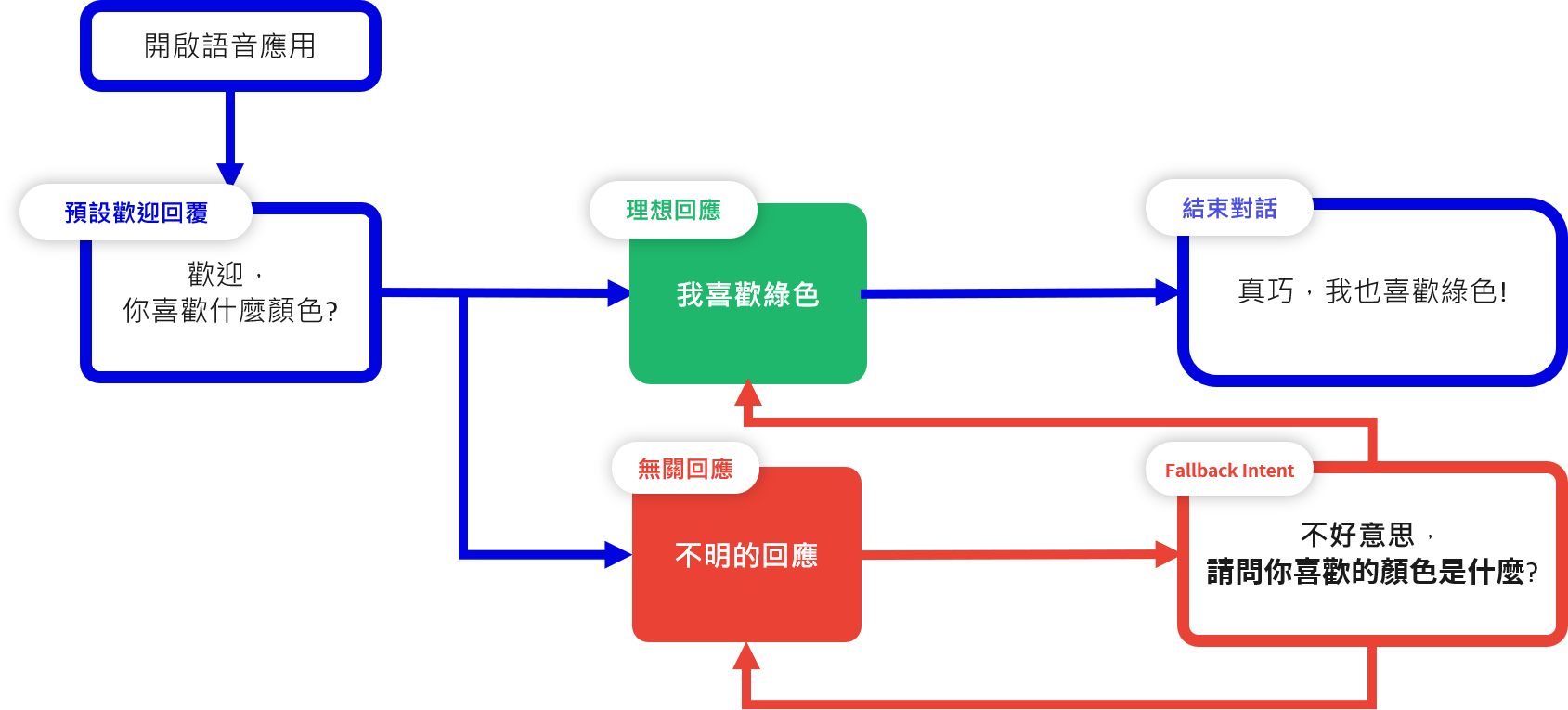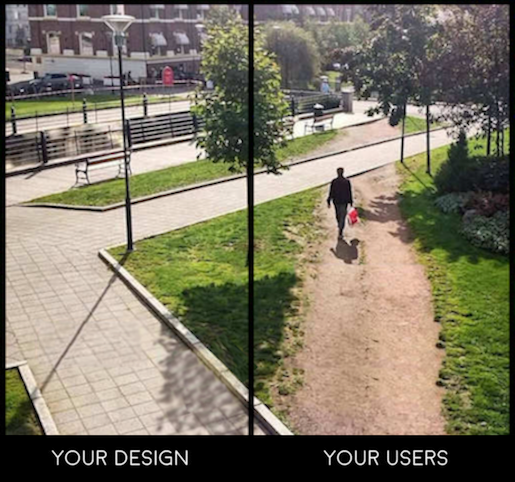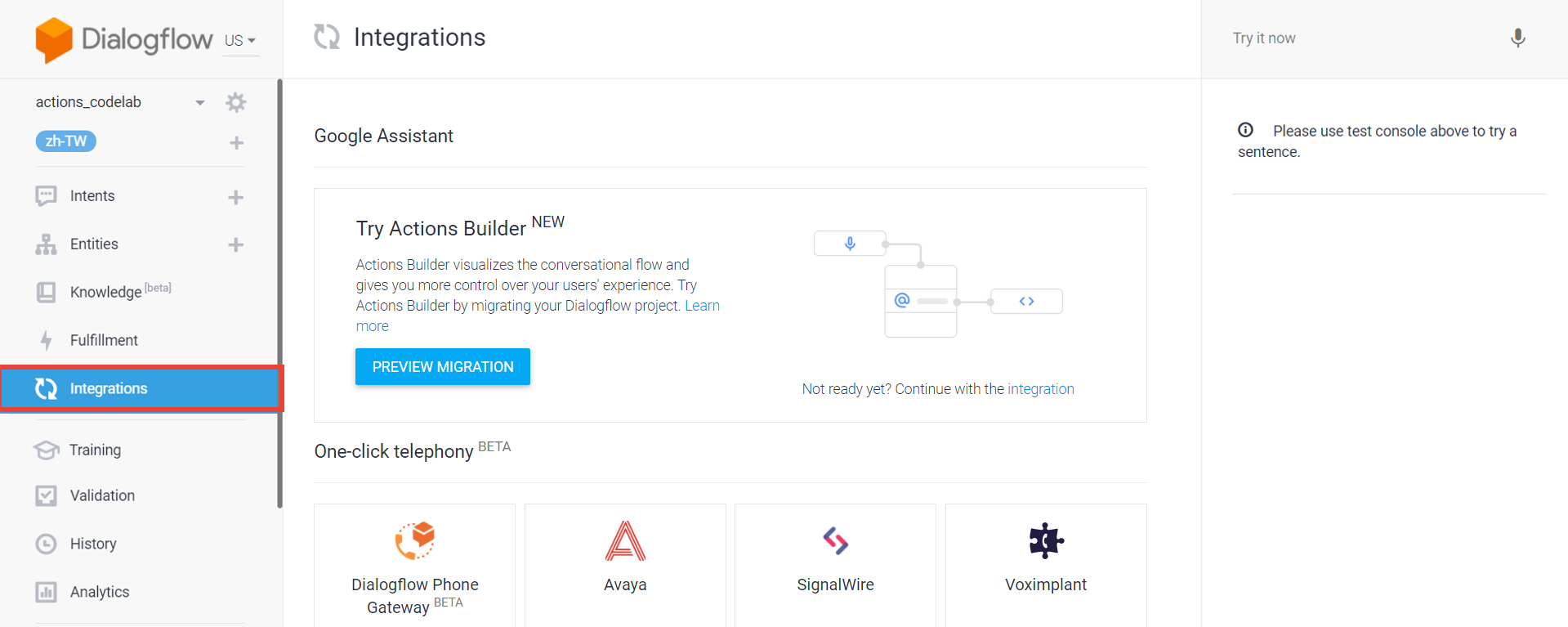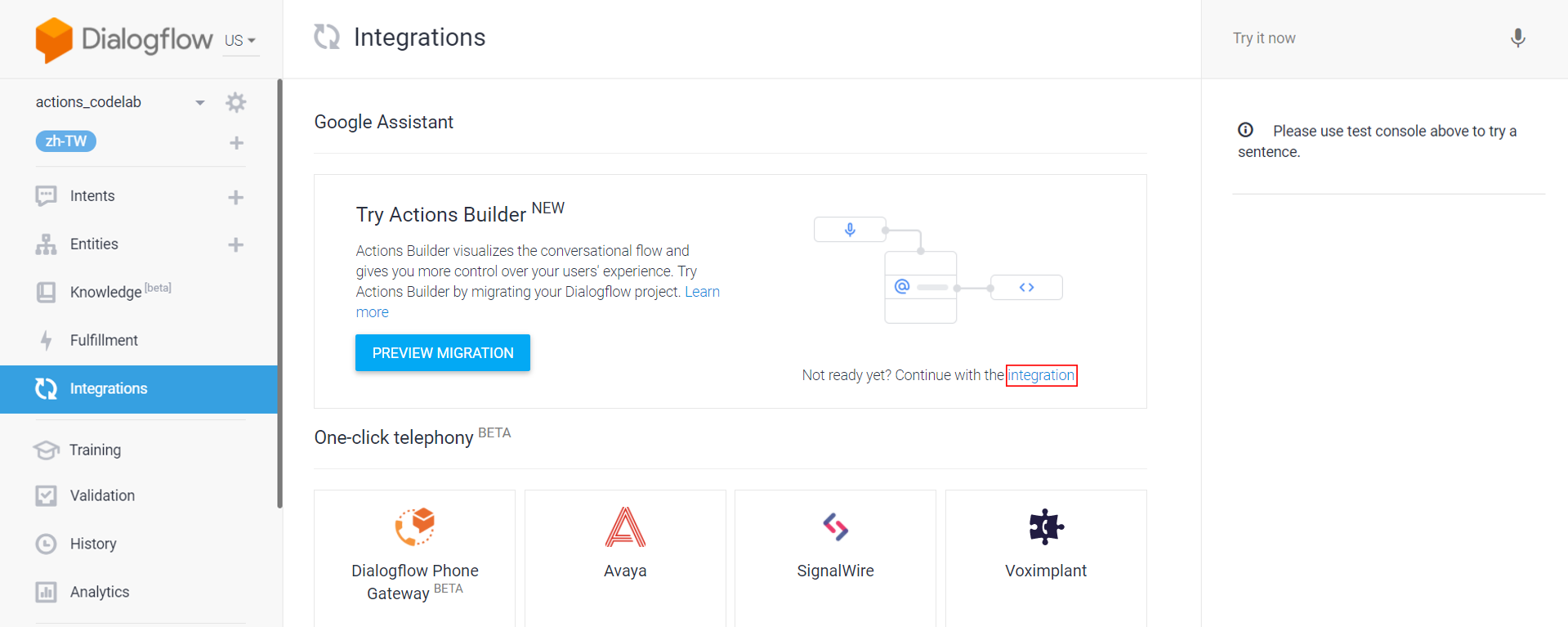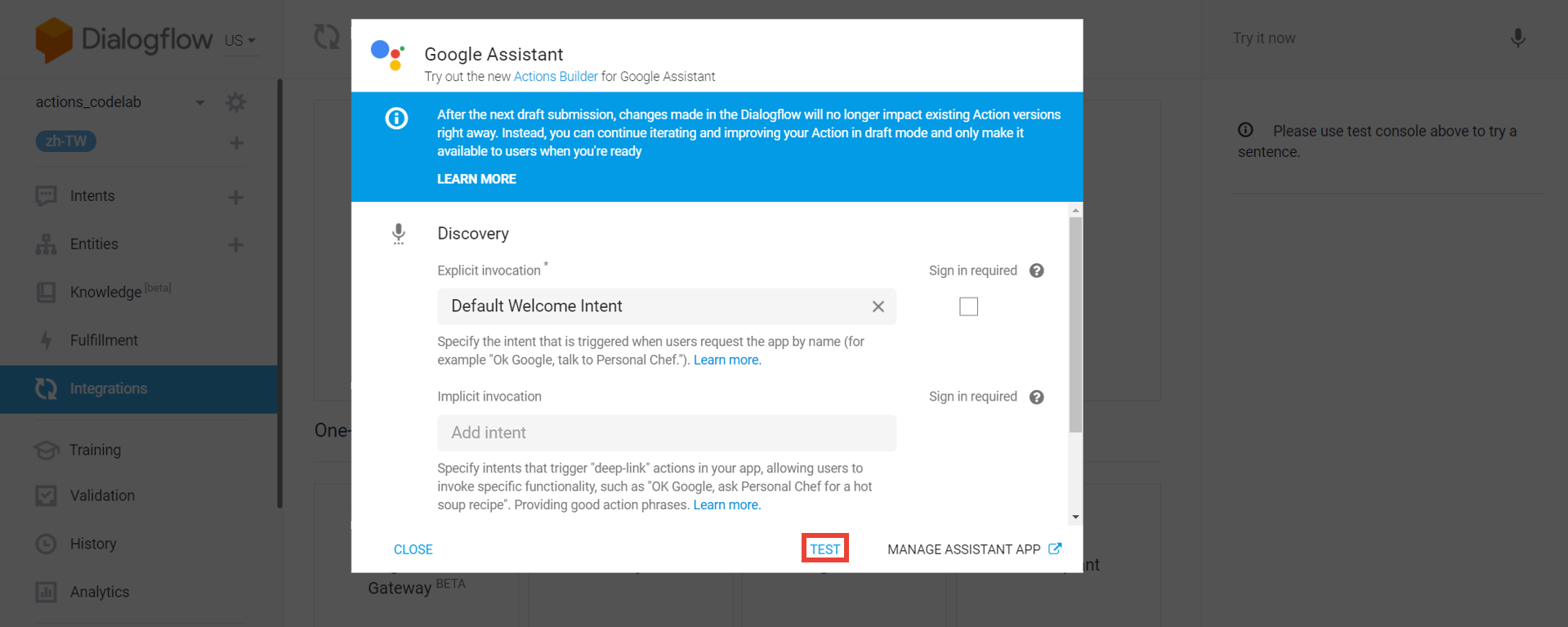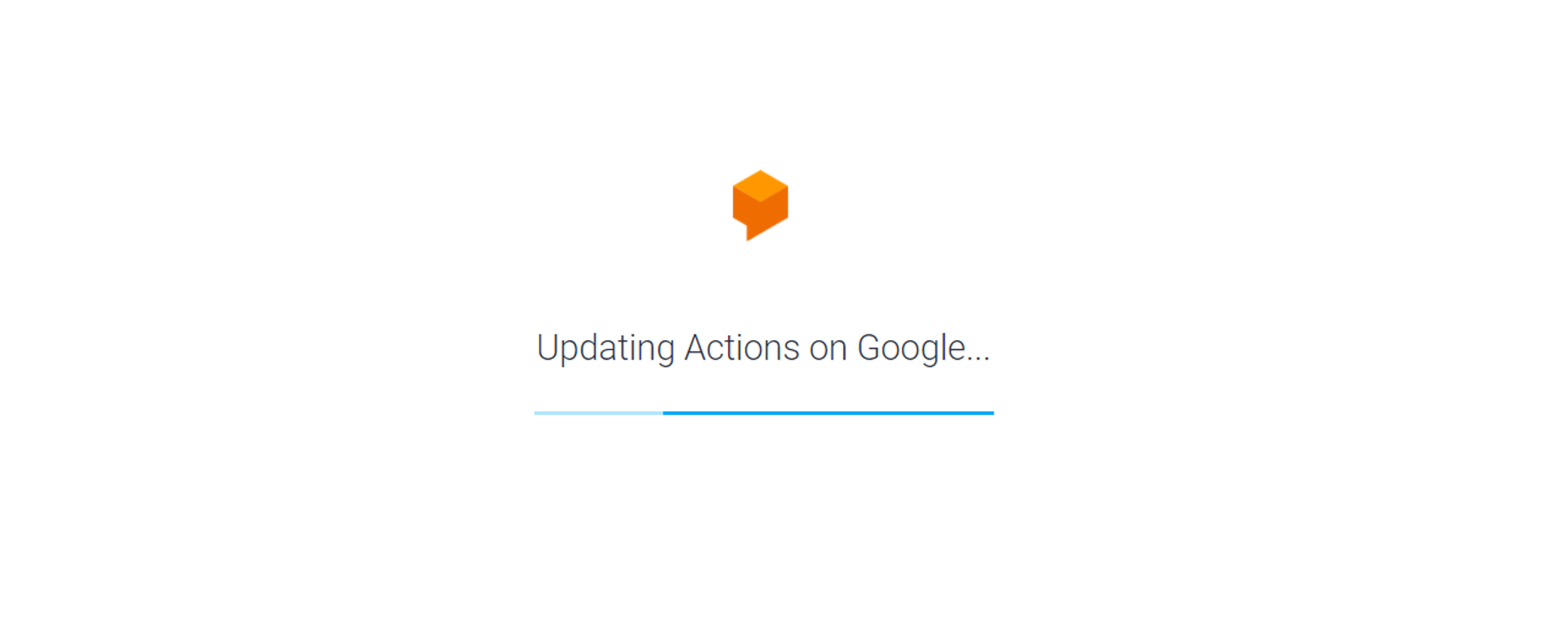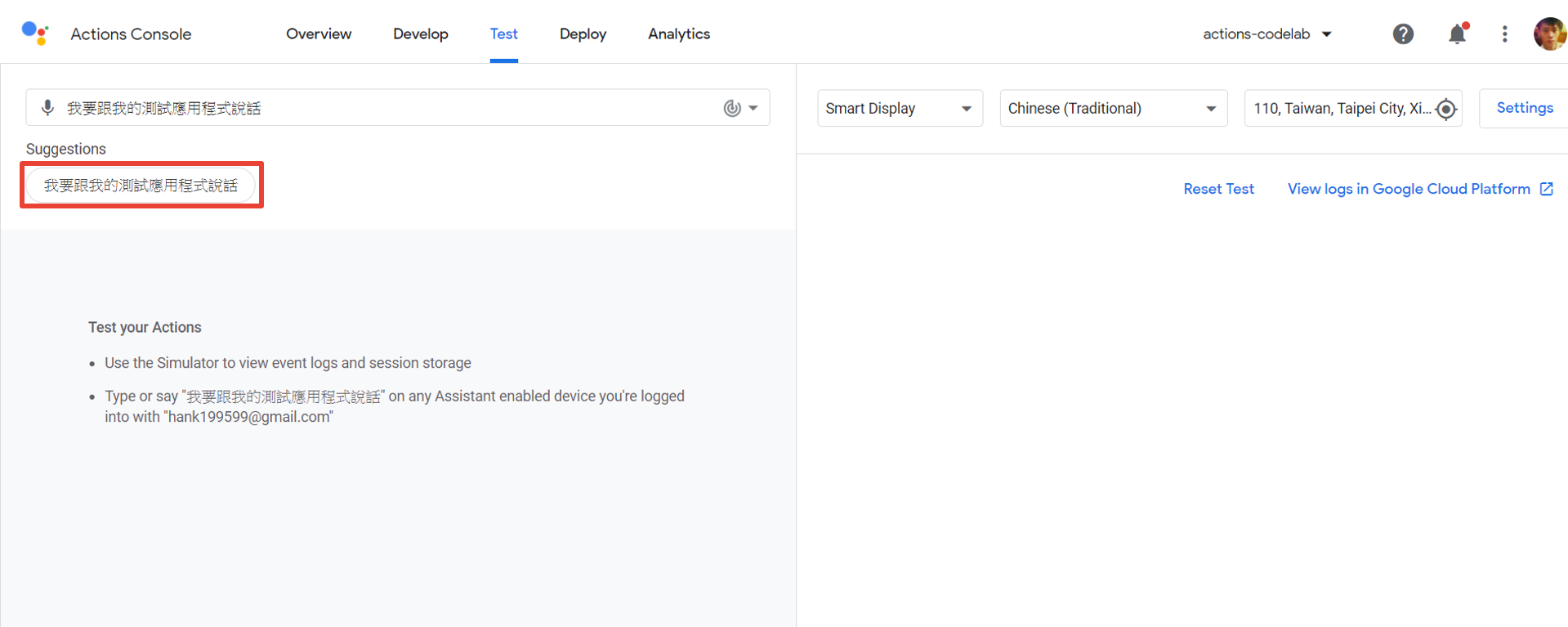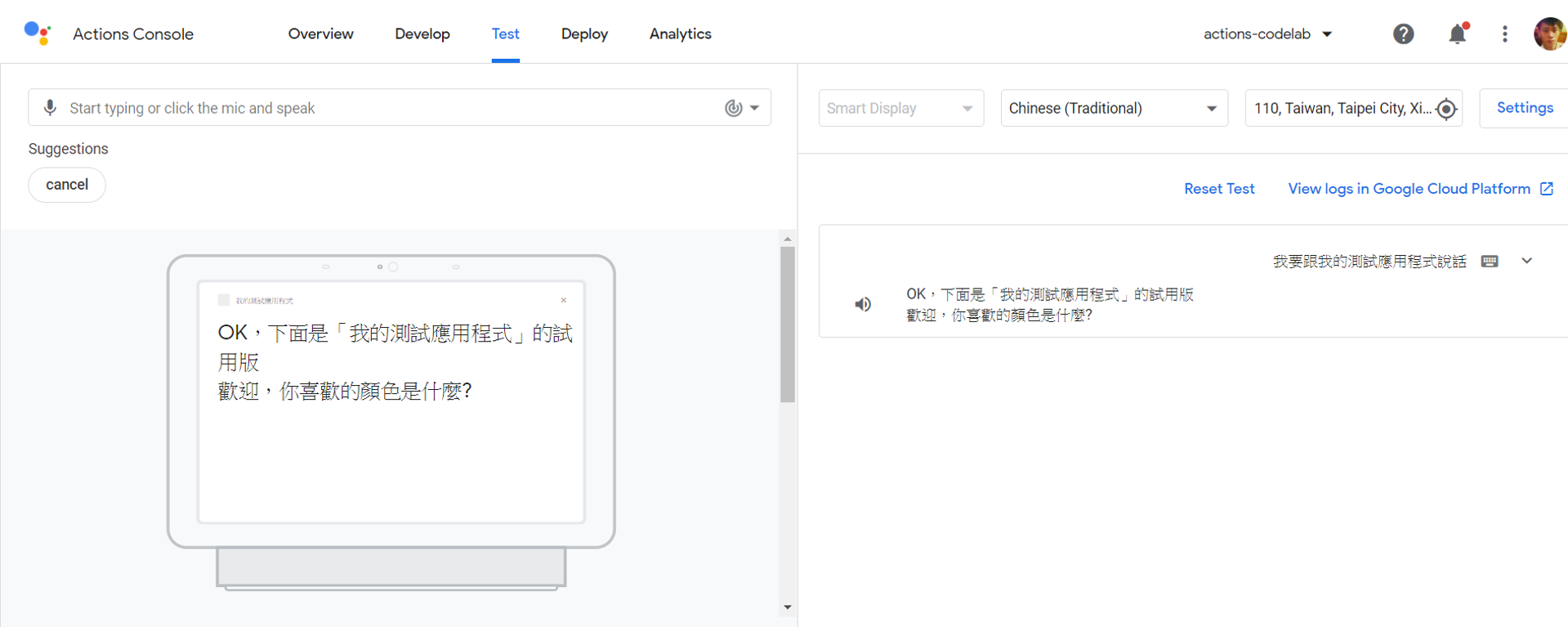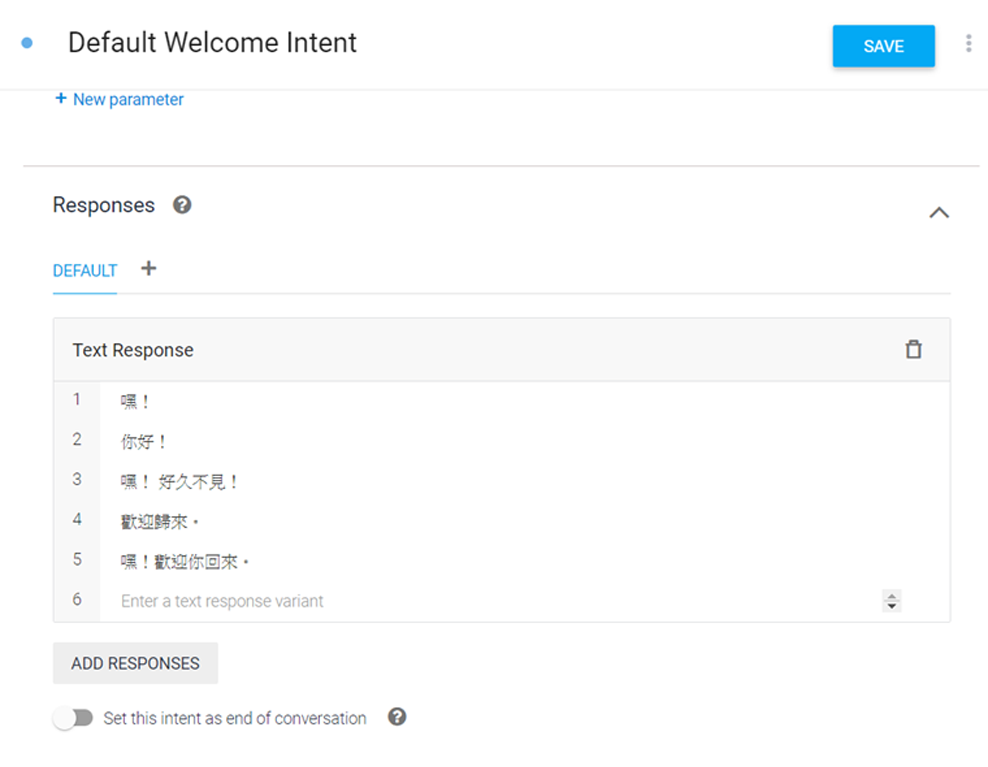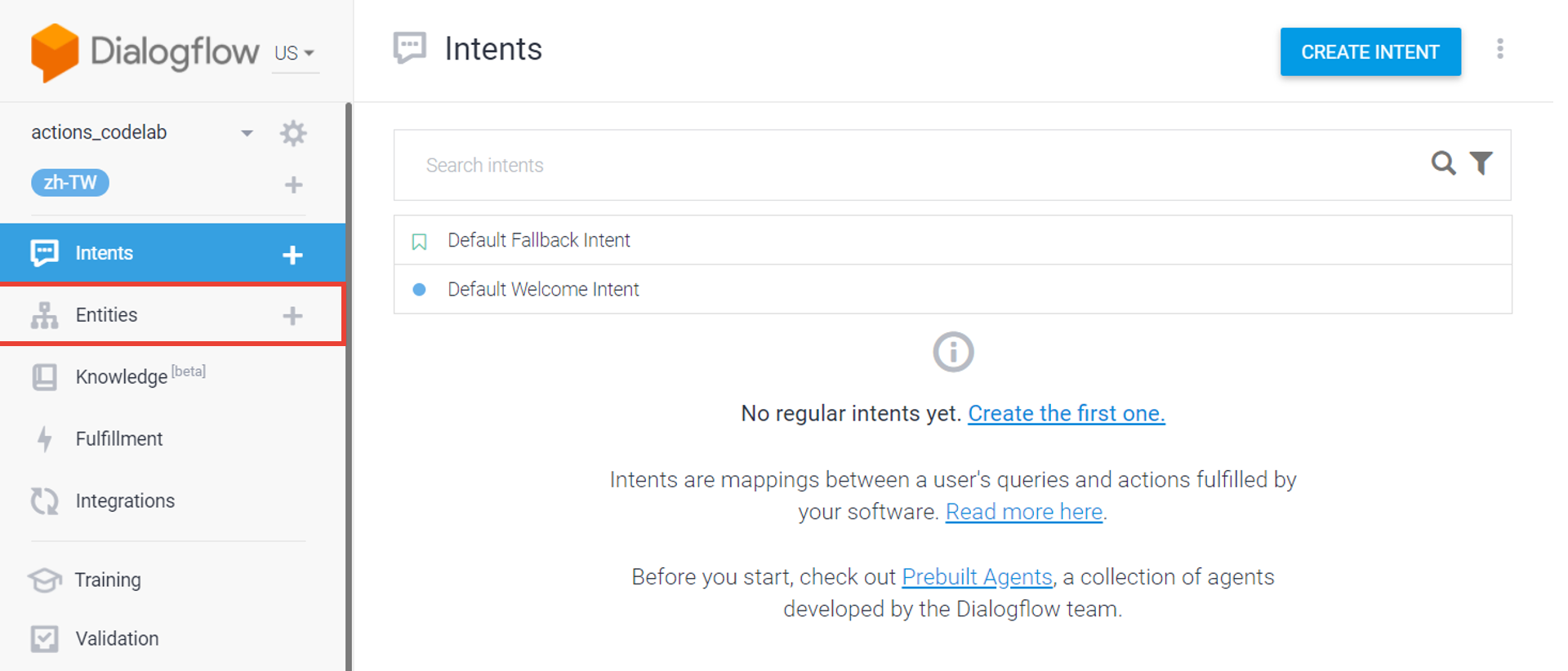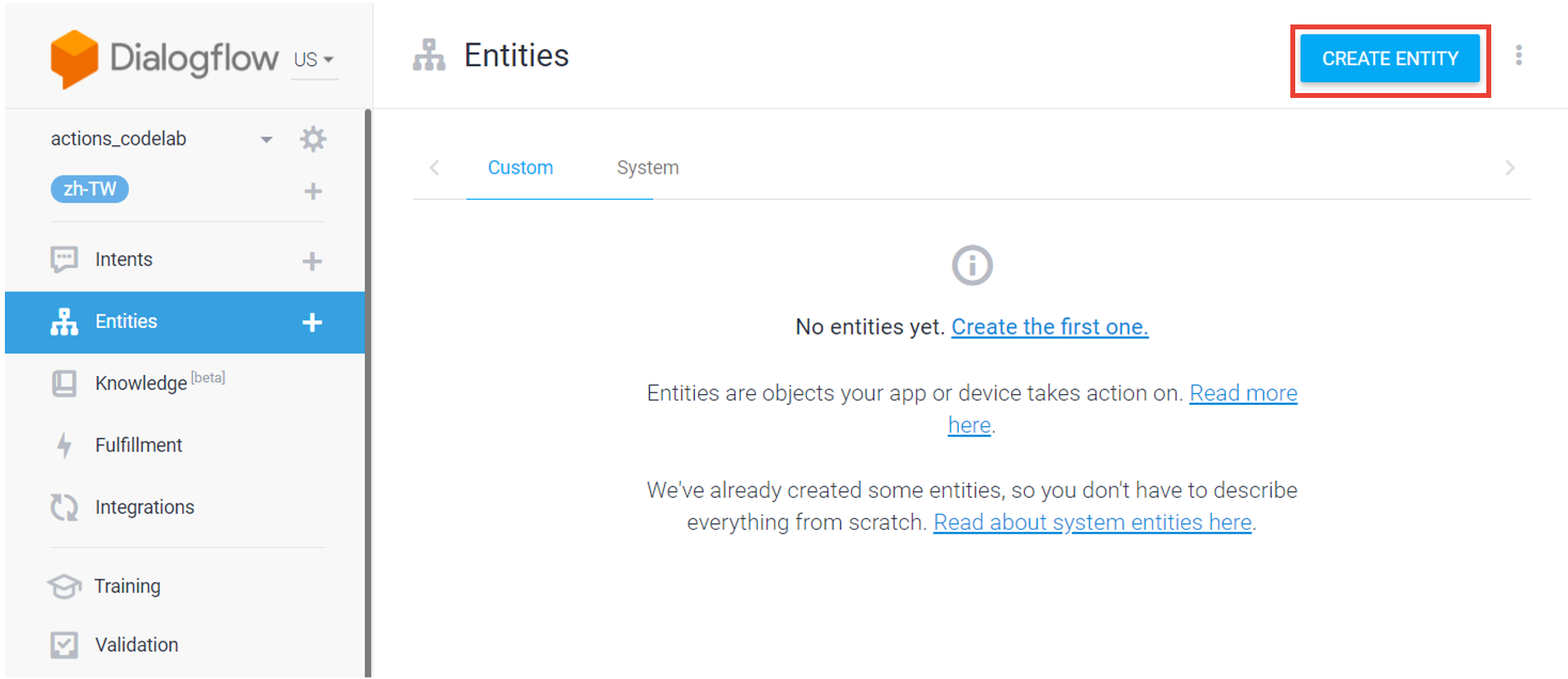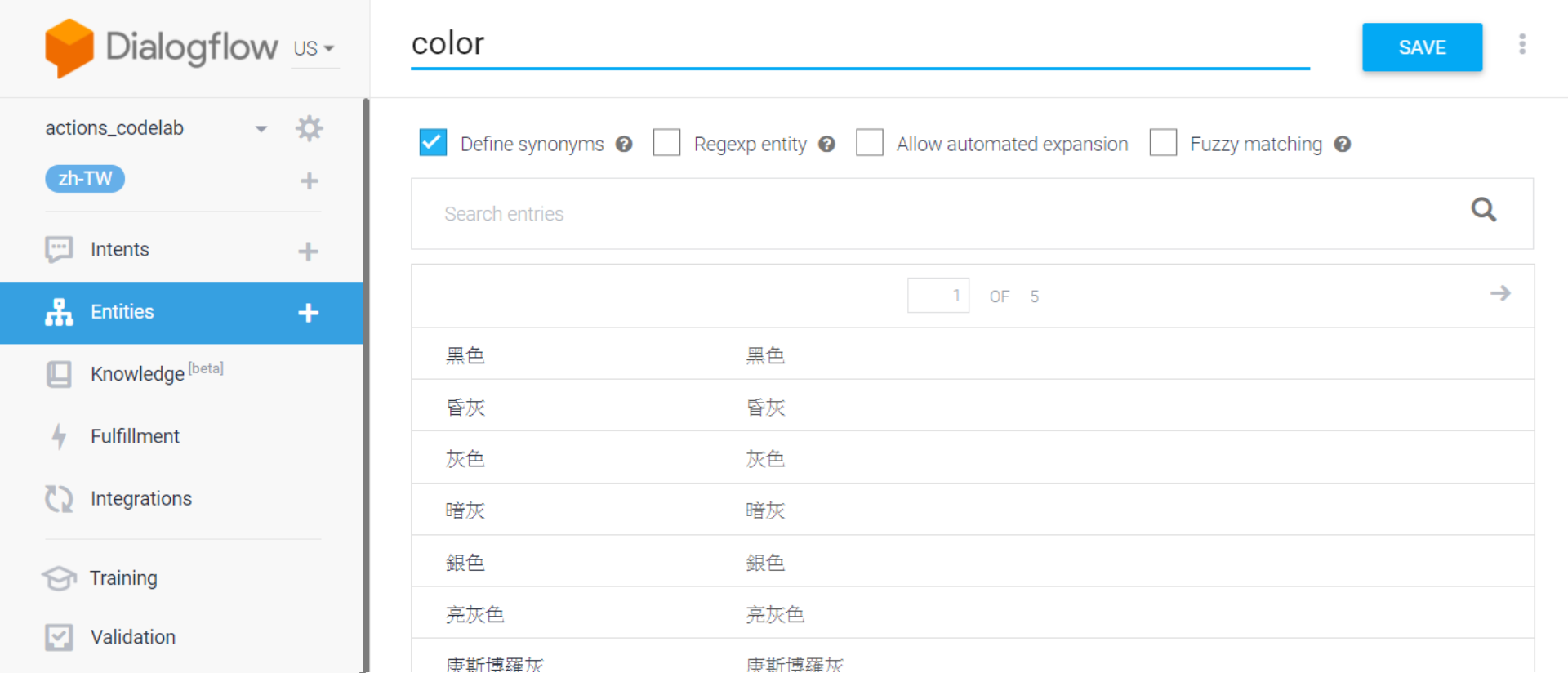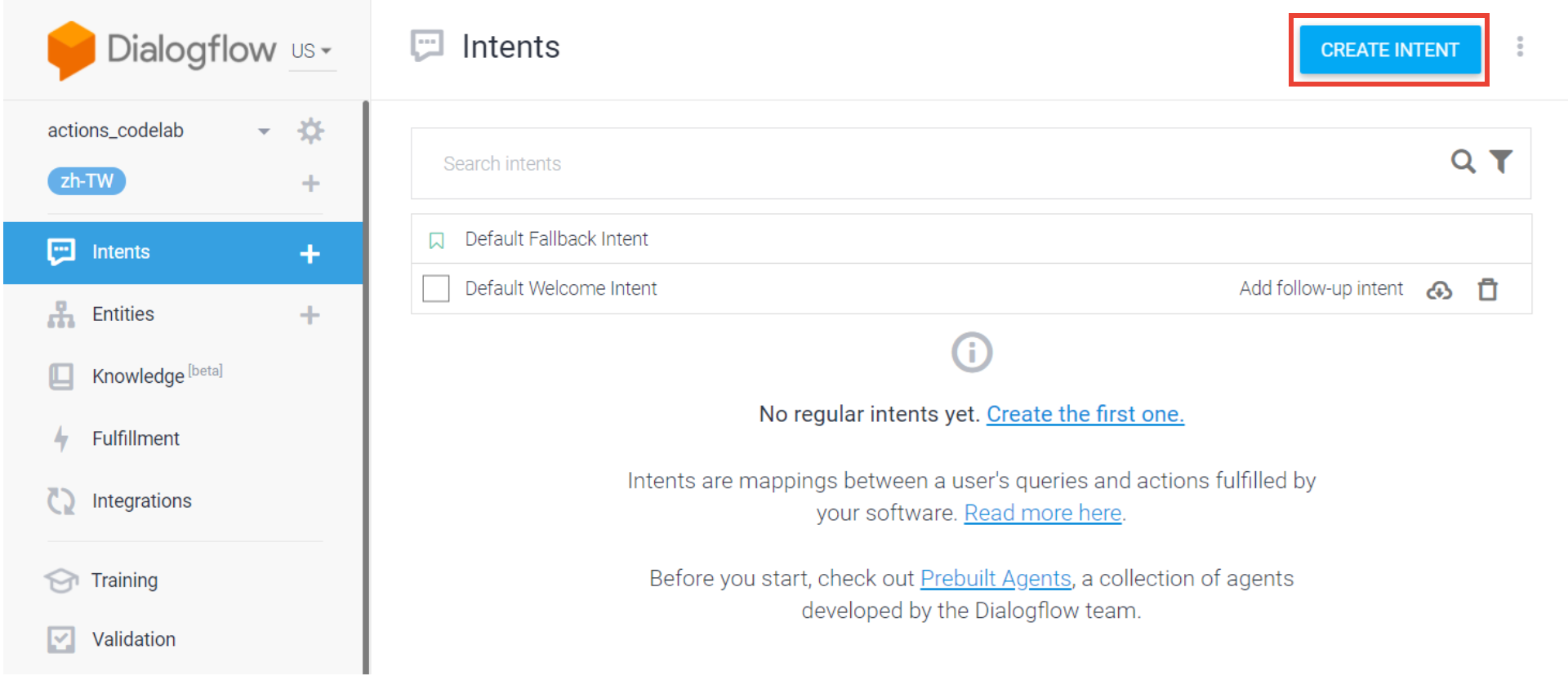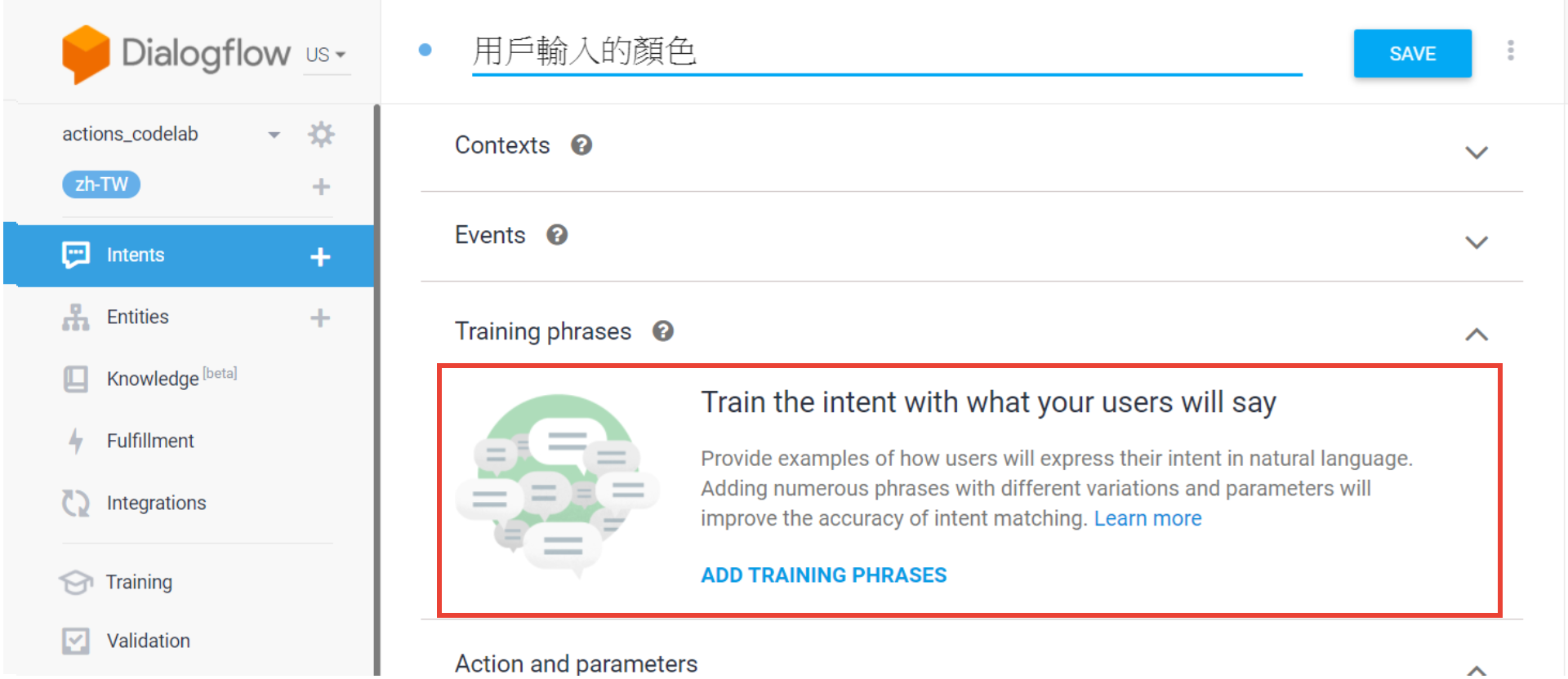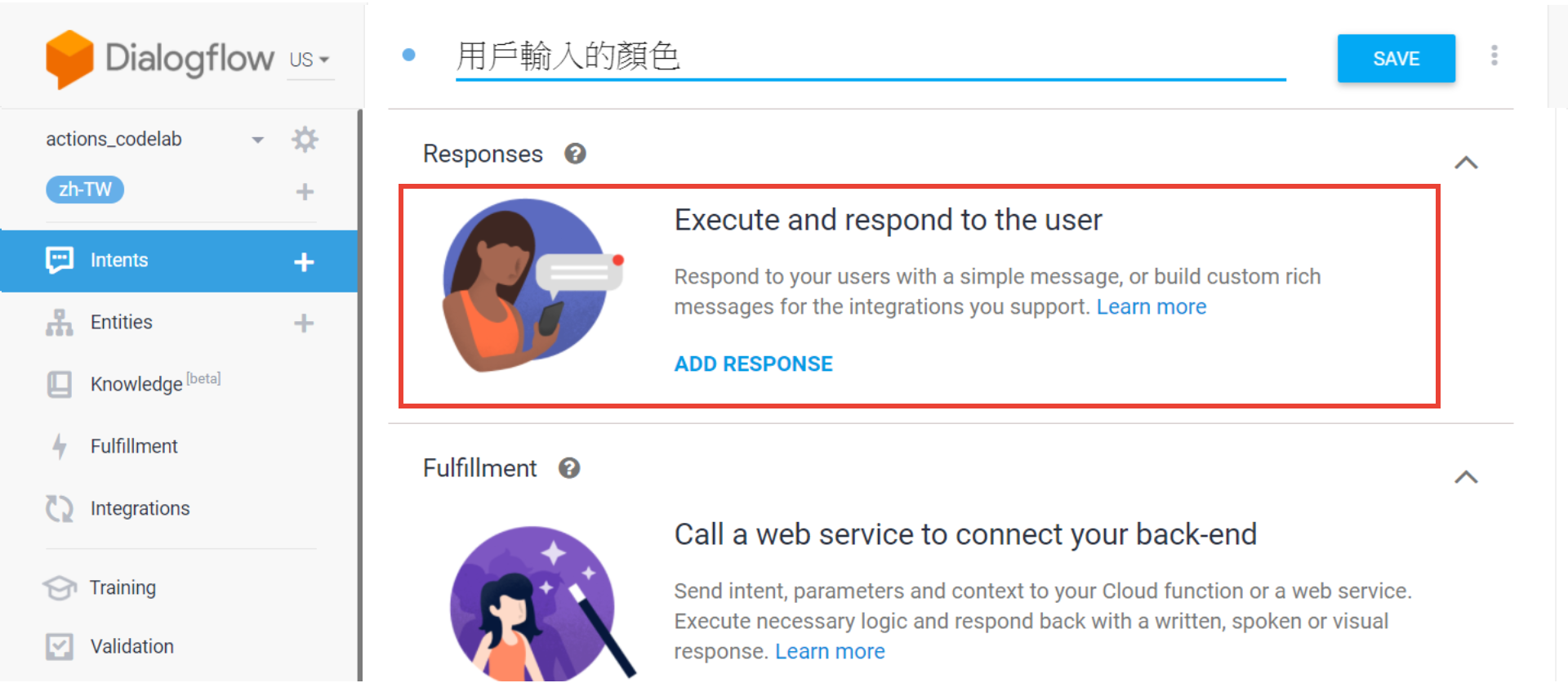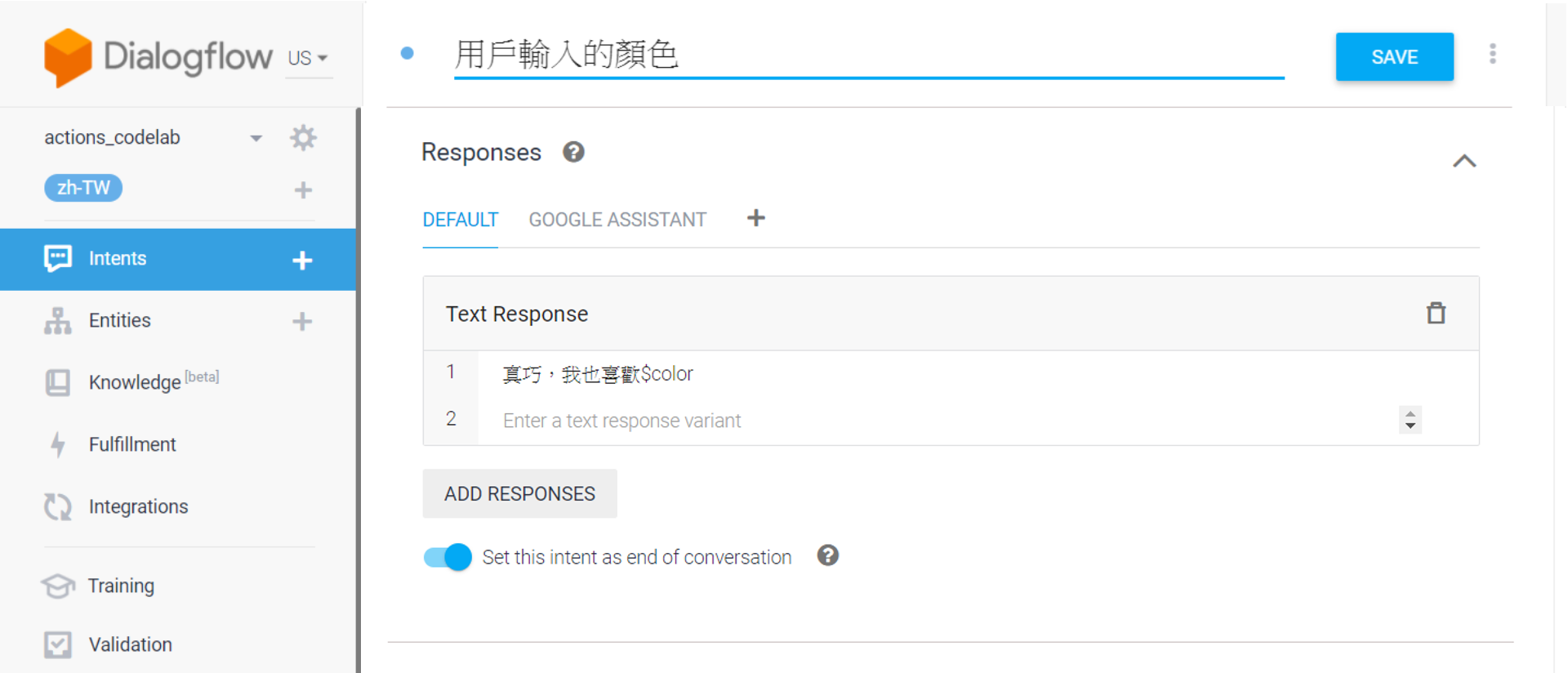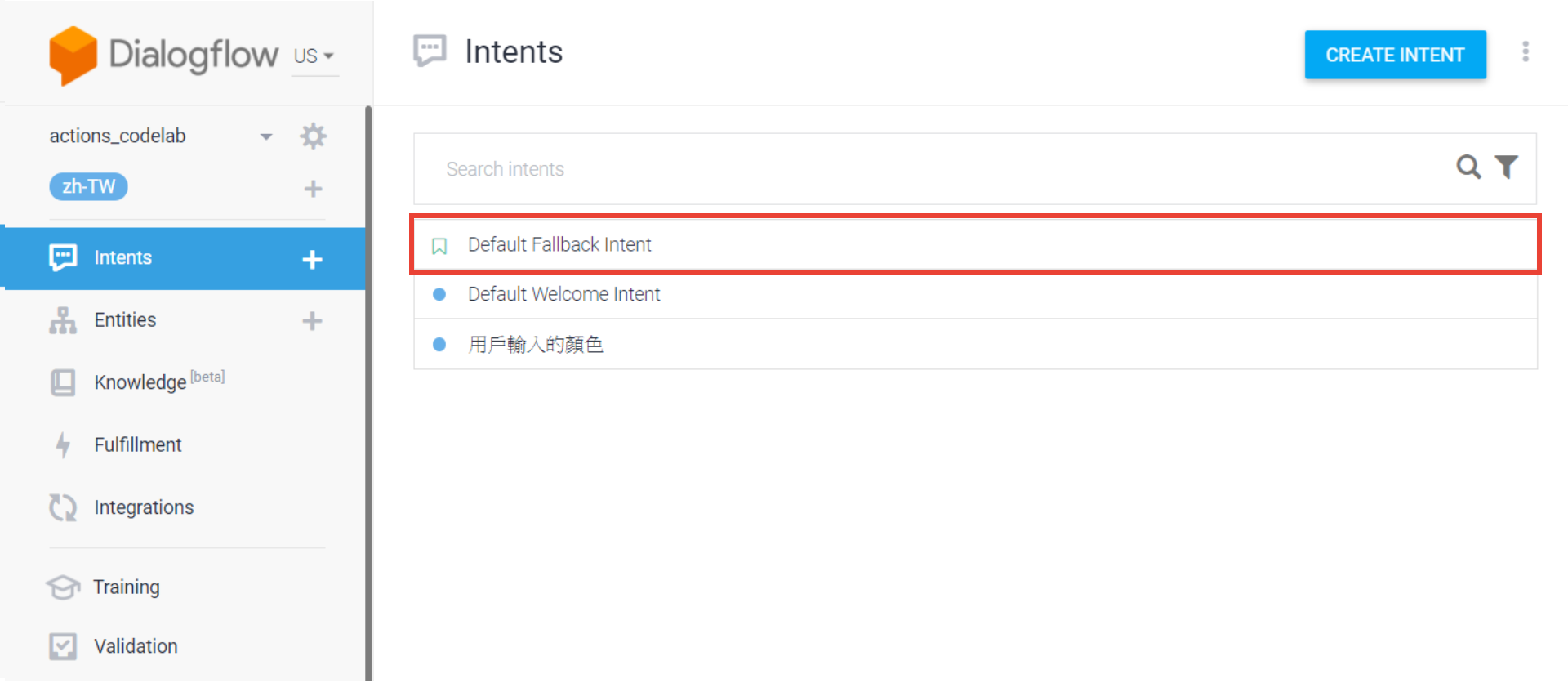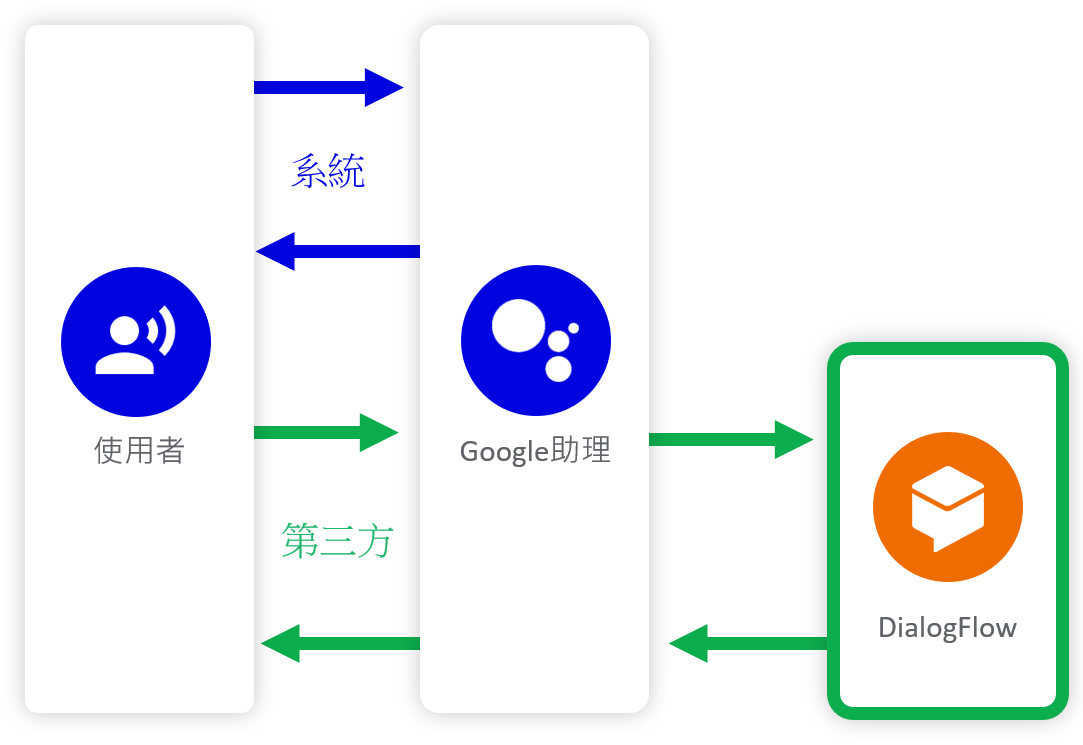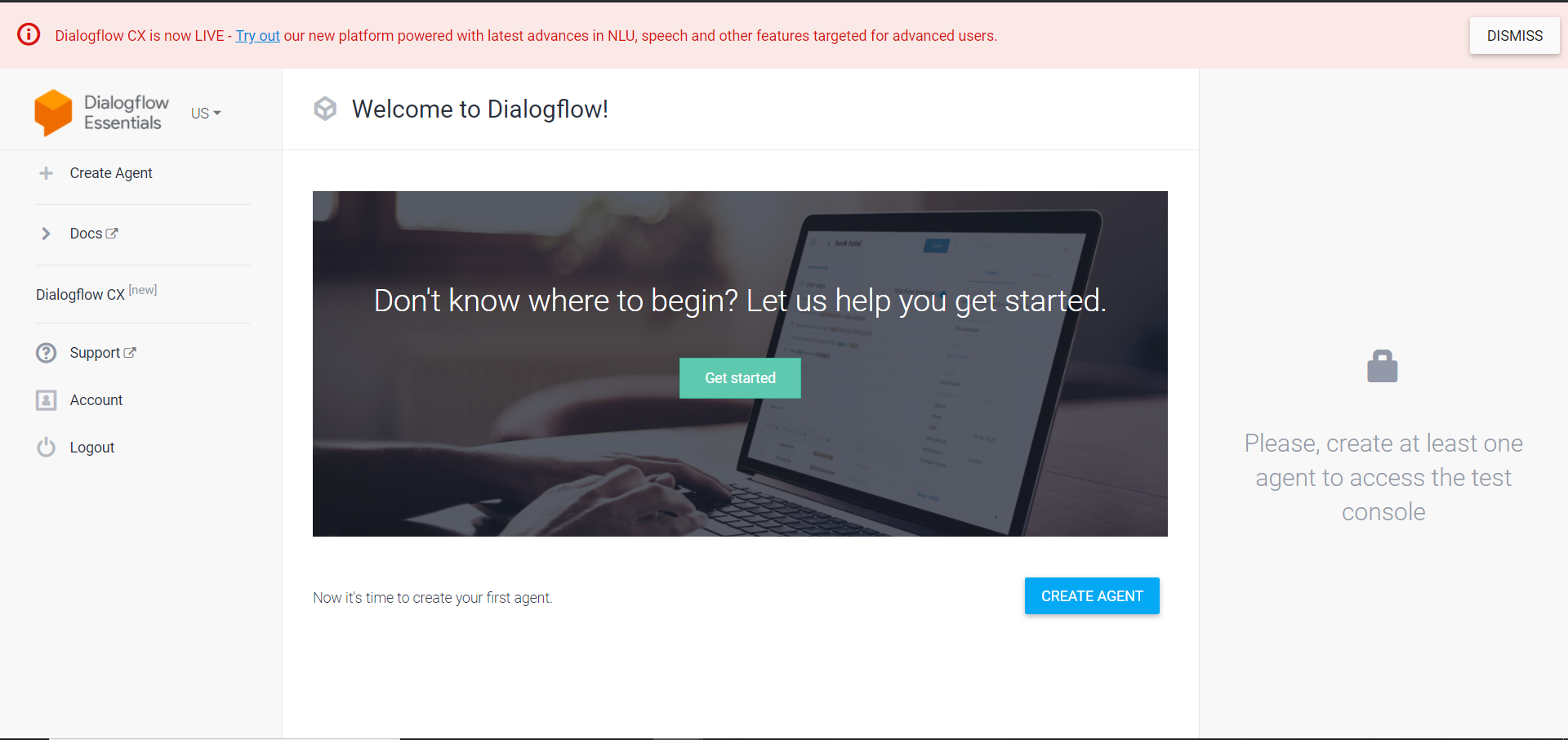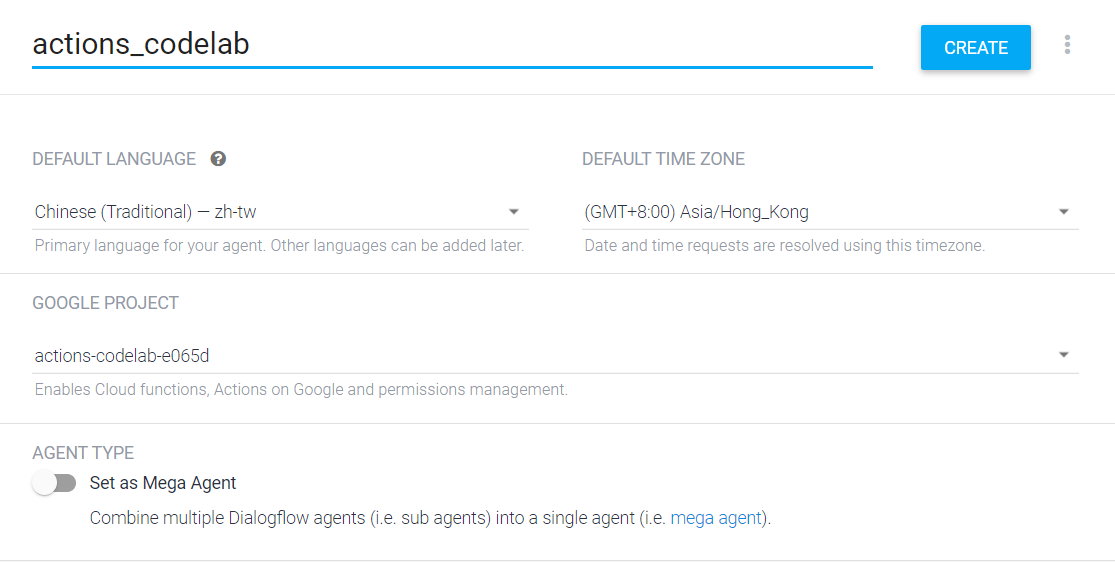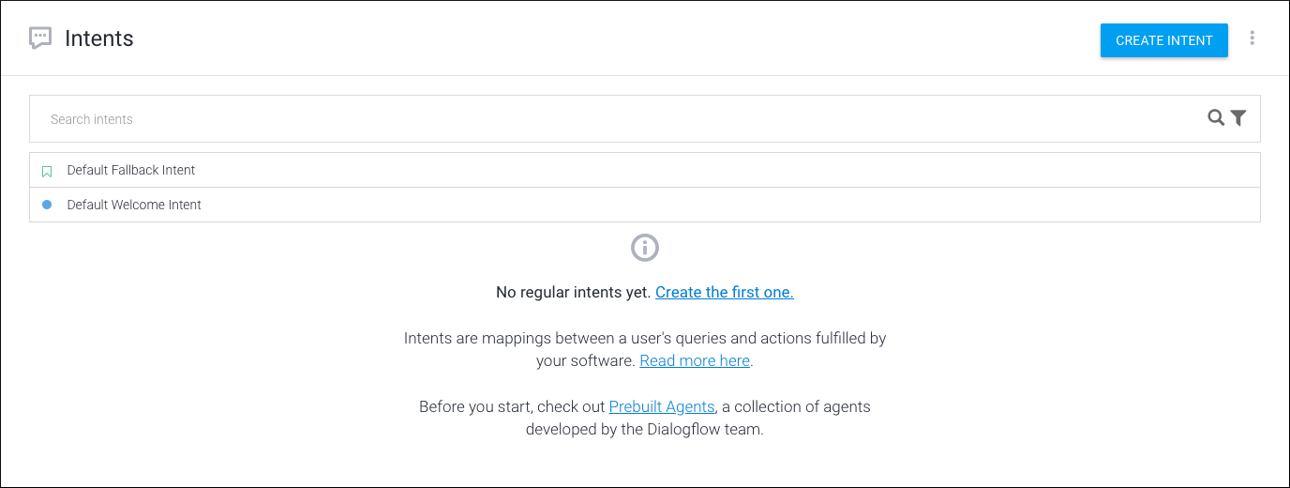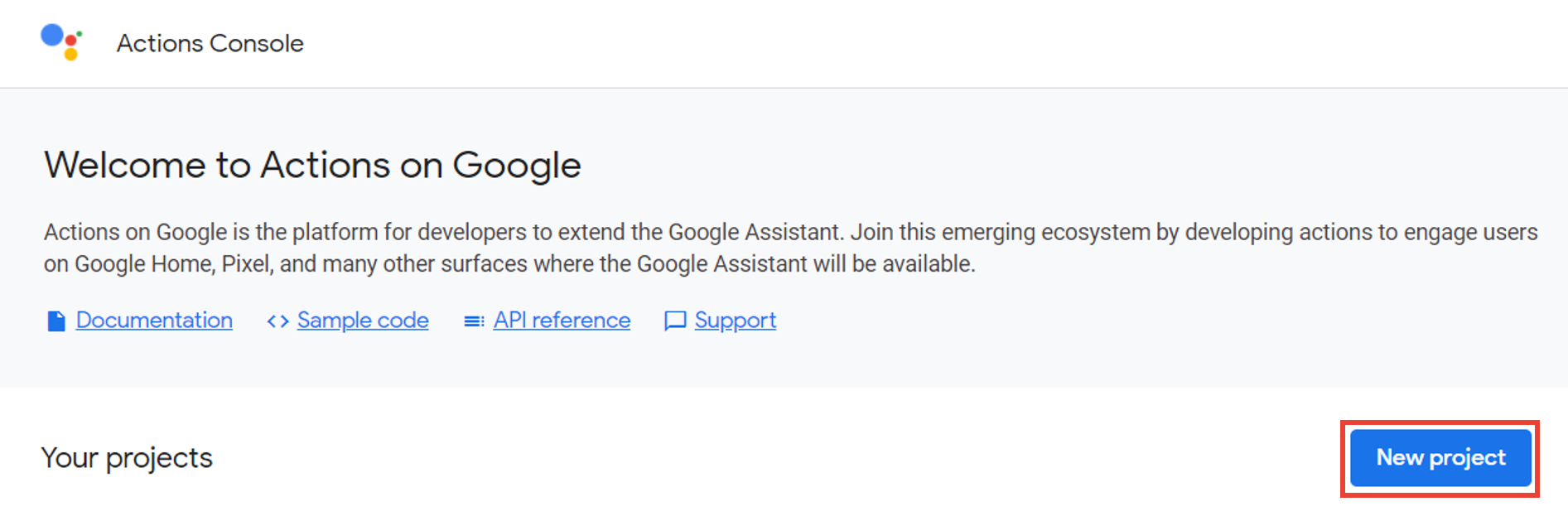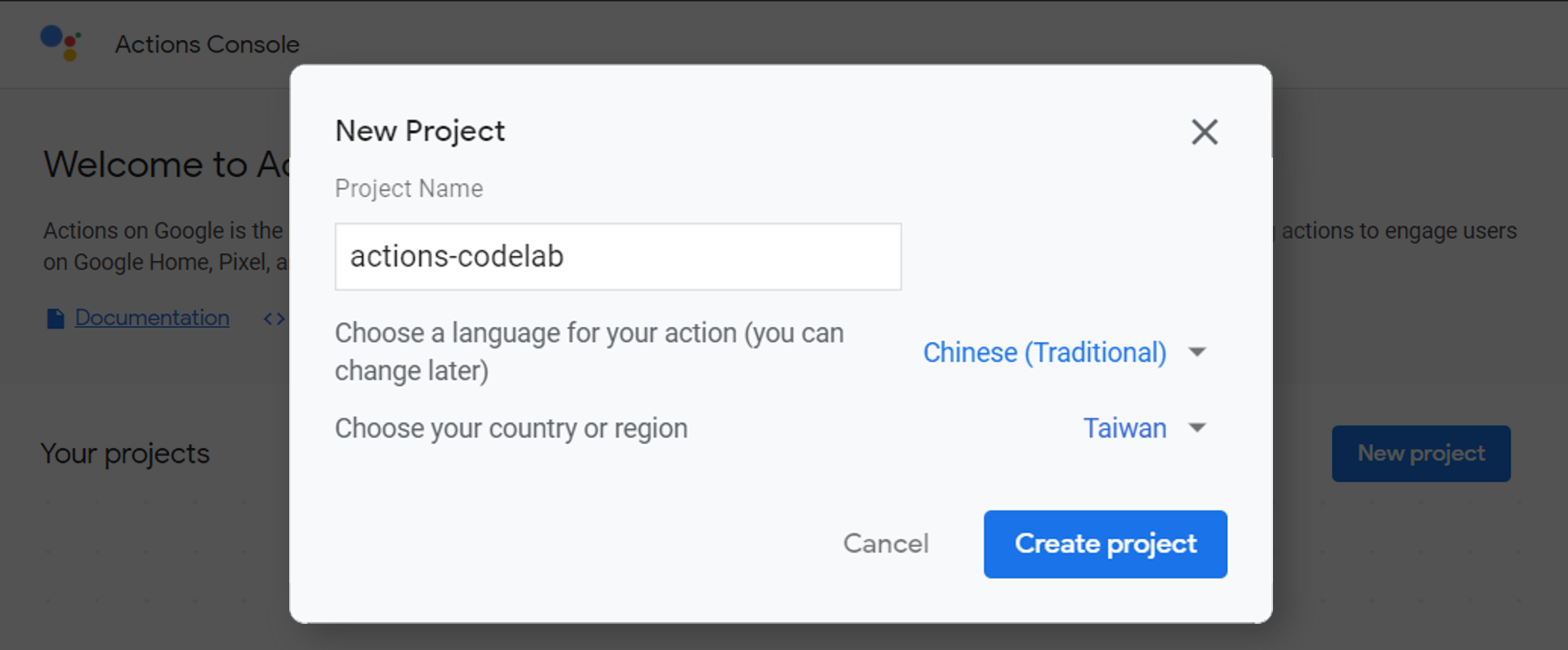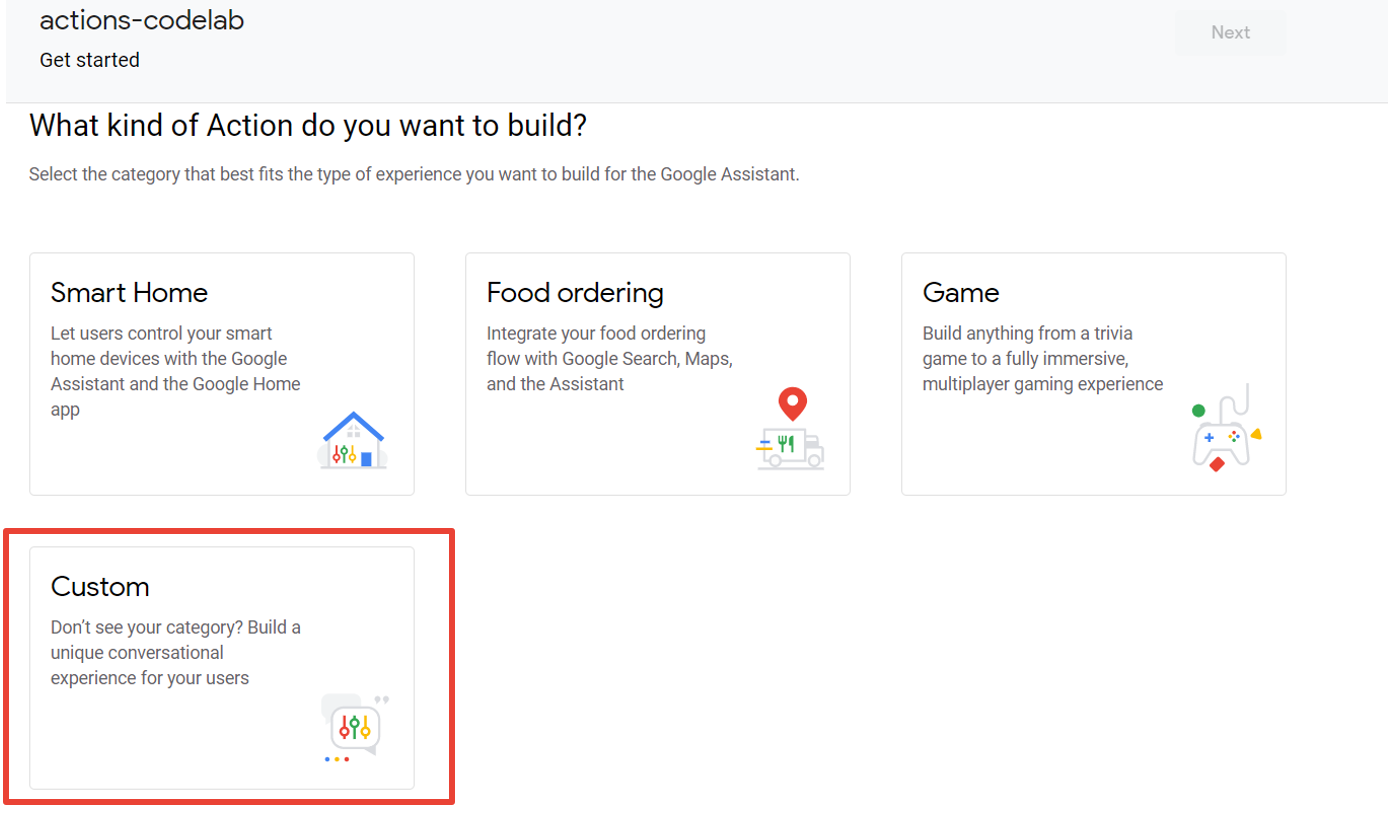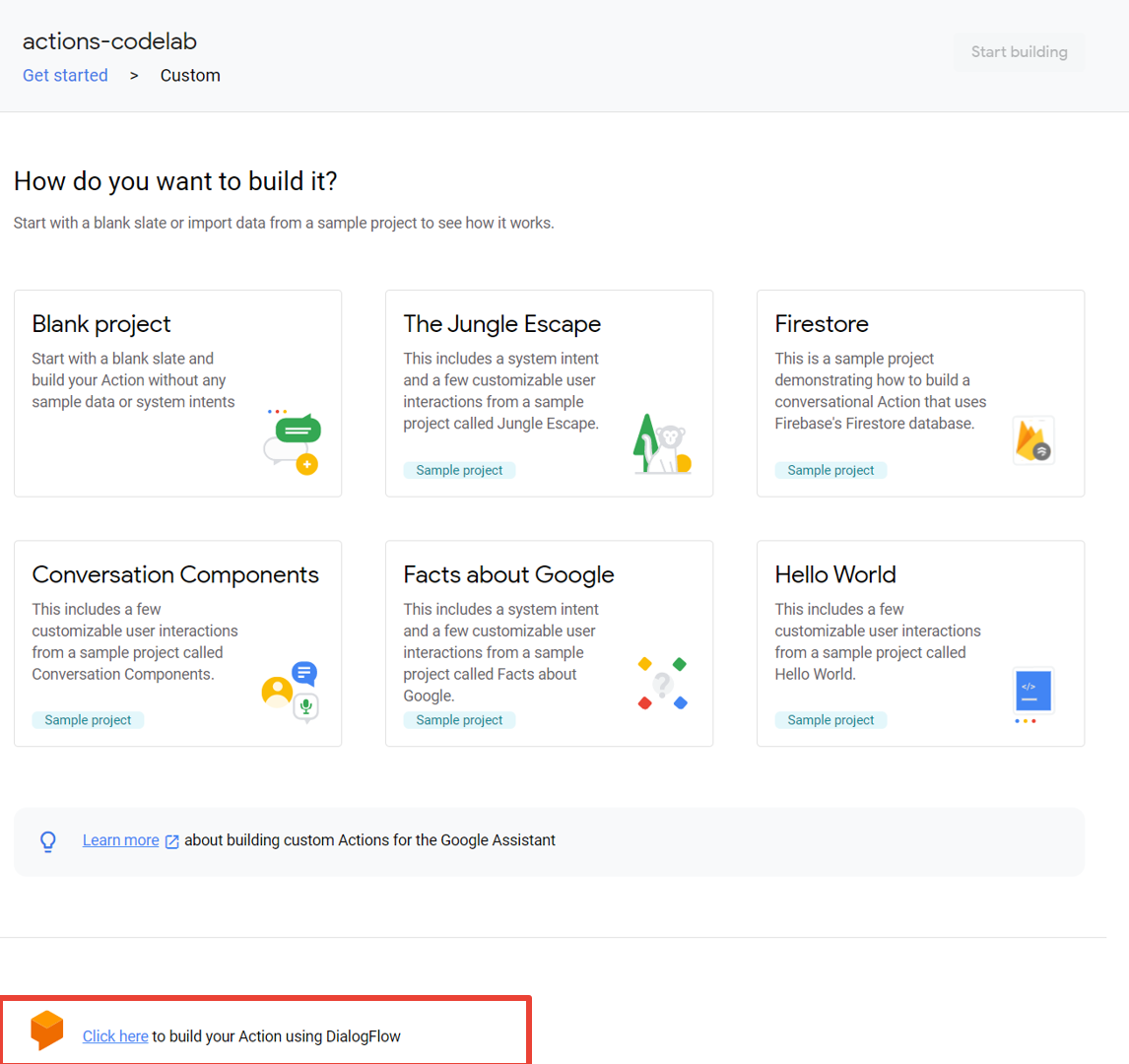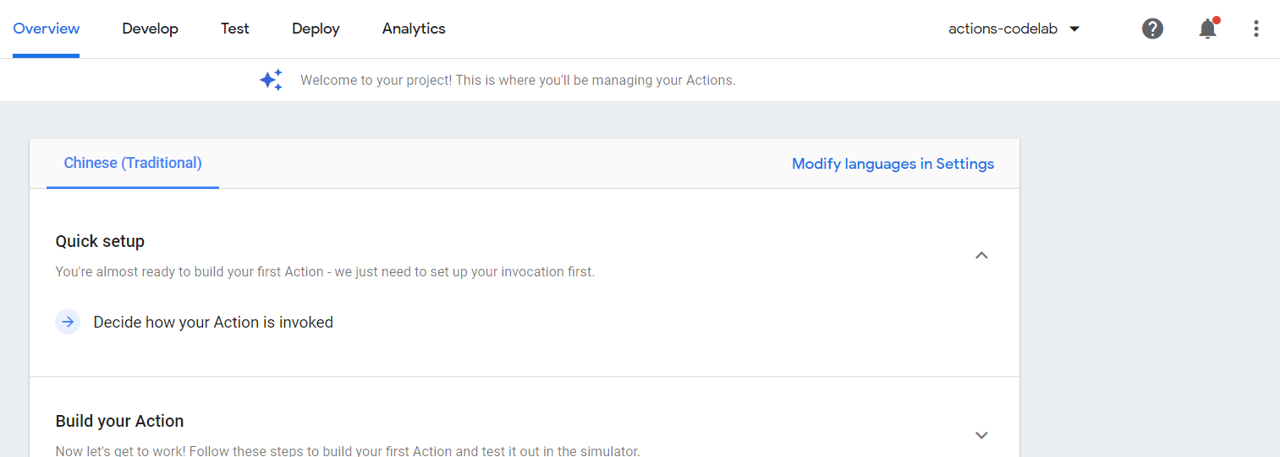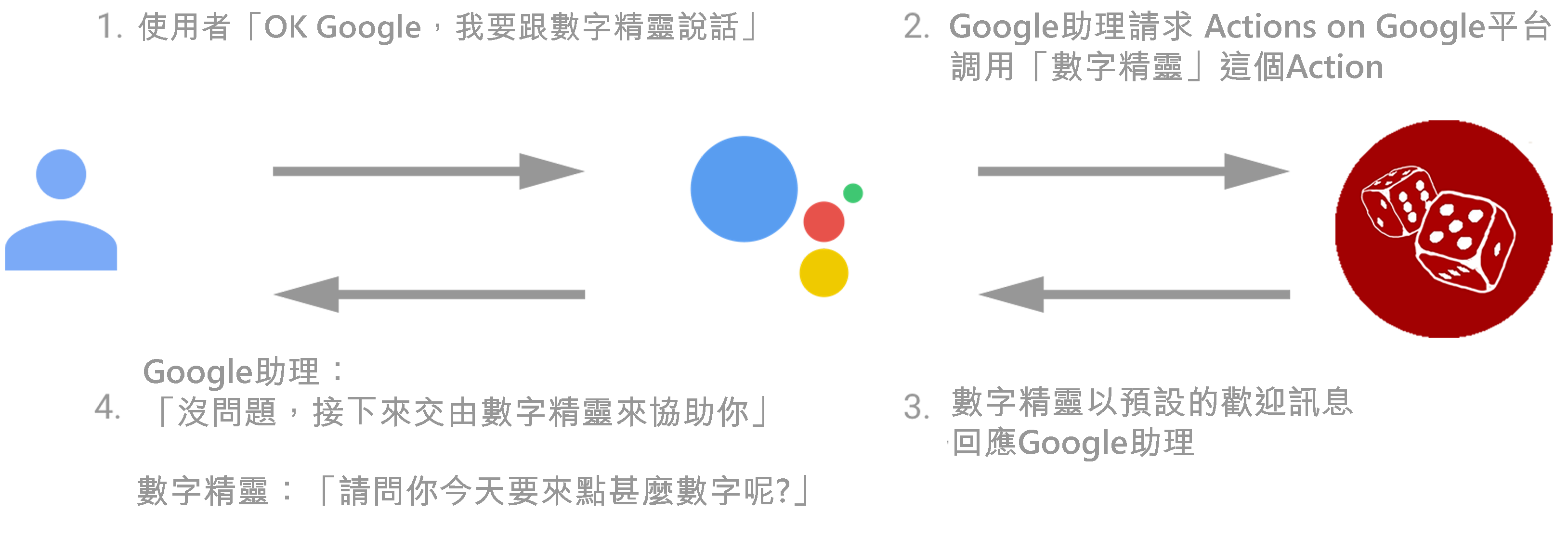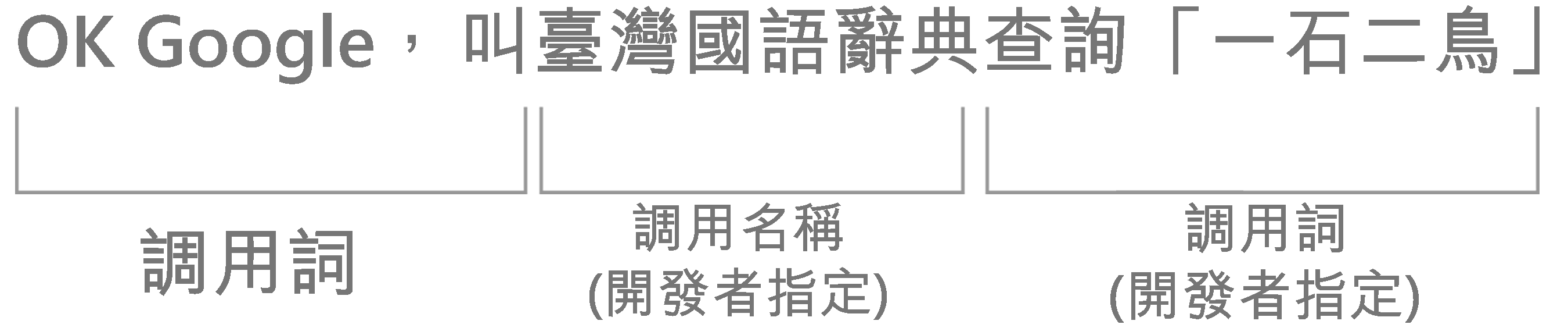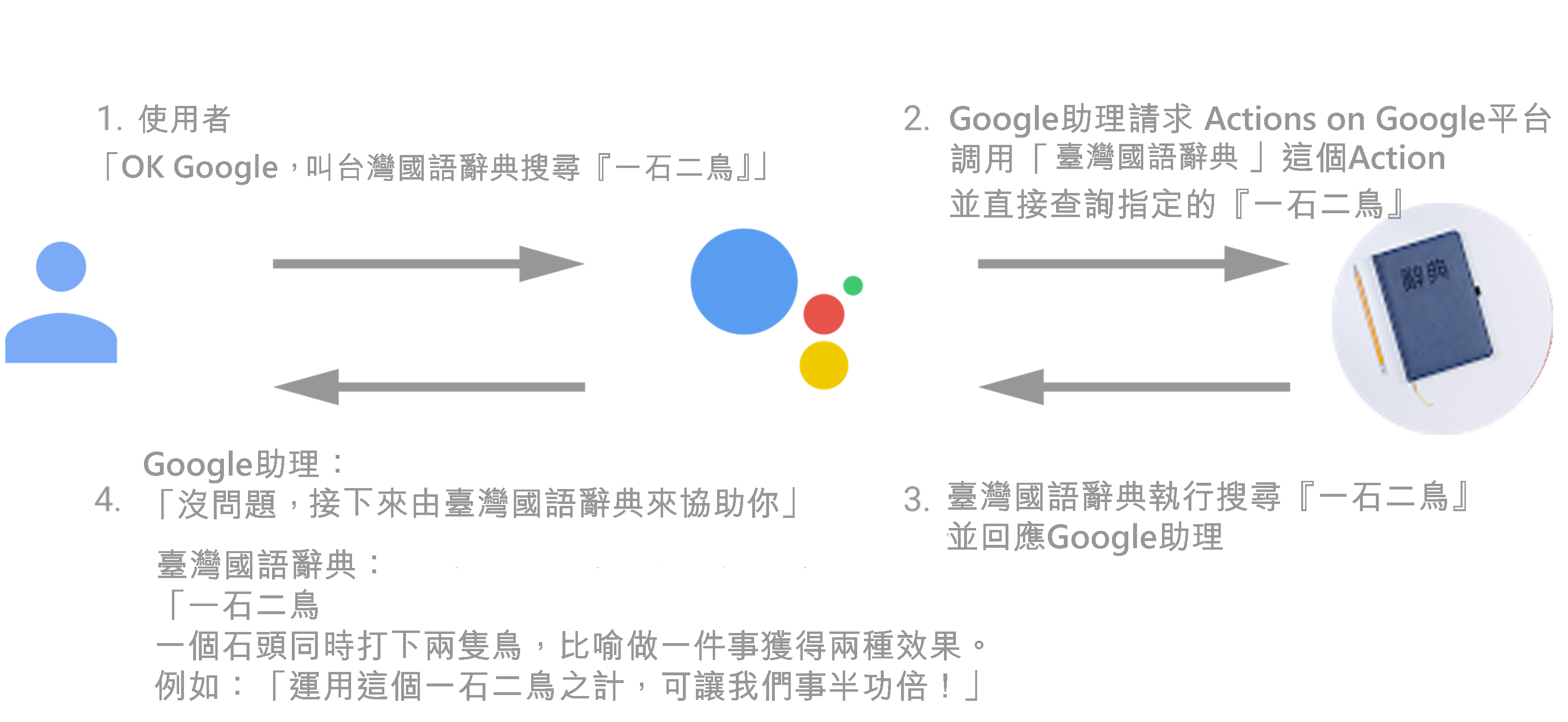書籍
- 《找到你的維他命人:人際關係中的痛苦、困惑、空虛,你不必自己承受》
- 作者: 瑪麗安.羅哈斯.埃斯塔佩
- 原文作者: Marian Rojas Estapé
- 譯者: 張懿慈
-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摘
P.30
如果一個人的童年因為性虐待、生活環境中遭受持續的身體或心理攻擊、在學校受到欺 凌或任何其他導致痛苦經歷的原因而經歷創傷,那麼他將來罹患情緒障礙、炎症或自體免疫 問題的風險更大,儘管心理、生理和行為的後果在成年期才被察覺,但在某種程度上,被觸 發的警覺性彷彿從那時起就一直潛伏著。
當我在會診時看到依附關係受傷、童年創傷很深與嚴重軀體化的患者時,我意識到他們 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處於高度警覺狀態,隨之而來的是身心俱疲,治癒那些傷口,平衡那 些炎症水平,並幫助改善他們的情緒是我的治療目標。
維他命人是催產素分泌的重要促進劑,有助於緩解緊張情緒。在困難時期給予適當的擁 抱可以降低皮質醇的飆升;自信的眼神可以果斷地幫助別人度過難關;幾句鼓勵的話就能打 破孤立感。
生活有時非常艱難,但我們有很好的工具可使用,並盡量以不痛苦的方式去應對它。
P.54
感性不再流行
當睪固酮水平過高時,男性往往更具攻擊性和衝動,並減少了慷慨的態度和同理心。有權有勢和身居要職的人通常以強硬和果斷為特點。除了少數例外的情況之外,這類人花較少的時間去感受團隊成員的情感。實際上,有關此問題的研究表明,注射睪固酮的人解讀周圍情感的能力較差。他們很難理解他人的處境。在分析他人的行為時,他們會貼上標籤並一概而論,而不會正確地深入研究情感。
我想澄清一件事:適度的壓力和競爭對於表現是有益的,也能正向地提升工作表現。這種正向的壓力能夠活化警覺系統,提高注意力和專注力。然而,如果壓力長時間持續存在,就會產生負面和有害的影響。
P.75 - 77
與你分享一個關於我的朋友胡安(Juan)在Glovo外送平台工作的案例。我總是把我的事情和約會事項寫在一本 Moleskine 記事本上,而且每年都會換顏色,歷年來的每一本都保存在抽屜裡,這樣能讓我回想起所經歷的事情。我把記事本放在包包裡,小心翼翼地保管著,以免遺失,有人建議我將它數位化,但我喜歡寫下來、劃掉和看到它們實實在在地呈現在紙上。
有一個星期三的早晨,我發現我把記事本忘在家裡了。有人通知我去開一個會議,但我記不得當天是否有其他事情。我需要我的記事本,於是我透過外送平台把它送到辦公室。過了一會兒有人敲門,是一位個子高高的外送員,他背著外送平台的了裝有記事本的包裹,然後他就離開了,我站在那裡查看有空的日期,突然聽到有人一邊講電話一邊啜泣,我走過去,看到外送員脫下了安全帽,哭得很傷心,我問道:「你需要幫忙嗎?」他答道:「沒有人幫得上忙,我的情況很嚴重,」我說:「我是處理嚴重問題的專家,也許我能幫到你。」我讓他進入我的辦公室,他把他的事情告訴了我。「我母親住在委內瑞拉,她病得很嚴重,需要接受治療才能康復,我和兄弟姊妹以及表兄弟姊妹們籌到了錢寄給她。剛剛我們收到通知,匯款公司把我們寄出的錢弄丟了,我母親無法接受治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手上還有一些待處理的訂單,但我現在整個人不知所措。」
我內心猛地一縮。他名叫胡安,身高大約一百八十公分,但看起來卻像個小孩子。他深深觸動了我,我花了一些時間安撫他並與他交談。幾分鐘過後,他回到工作崗位,我告訴他隔天再來找我。
我再次見到他時,他已平靜許多,而且有了解決問題的計劃。他看到我桌上的書,便問我該如何讓好事也降臨在像他這樣的Glovo外送員身上。
我沒有絲毫猶豫,對他說:「外送員前往顧客的家,但與顧客產生的接觸幾乎是無法察覺的,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無法看到對方的臉,因為安全帽遮住了視線,而這個瞬間通常不超過十五秒,我建議你在工作中投入熱情和熱忱,原因有二:第一,當你在生活中注入熱情時,你的大腦會產生重要的神經變化;第二,當你從熱忱中行動時,人們能夠察覺並感受到,美好的事情就可能發生。」懷有熱忱的人會成為「維他命人」。當然,我也向他提到了催產素。
幾個星期後,胡安打電話給我,他去馬德里市郊送外賣。過去幾天,他改變了他的「交貨方式」:他脫下安全帽,微笑地向開門的人打招呼。
接著,某一天中午發生了一些事。他送一份訂單到一戶人家的花園裡,並友善地告訴對方食物還是熱的,他在廚房聽說如果重新加熱,食物會失去風味。屋主非常客氣地告訴他,明天早上他將開始面試招聘一名司機,屋主正在尋找一個友善、值得信賴而且熱愛工作的人。當他問胡安是否有興趣應徵時,胡安回答說要諮詢一下他的心理醫生。屋主感到驚訝,他不明白為什麼胡安要打電話給我。
「為什麼你要諮詢你的心理醫生呢?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情嗎?」我告訴胡安他必須告訴對方全部的真相。
兩天後,胡安再次拜訪我。「我誠實地敘述了我的故事和我母親的疾病,他雇用了我。瑪麗安,你的建議對我有很大的幫助,我衷心地感謝你。」
我喜歡談論胡安,因為我相信他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在生活中懷著熱情並帶著自信工作可以改善身心健康,並且創造無限的機會,我相信建立起充滿催產素的連結會改善他的就業狀況,當然個人狀況也會一併改善!那位雇用他的先生在銀行工作,他幫助胡安籌措了他母親治療所需的資金。
P.78
工作場所是我們與人接觸最多的地方之一,人們會在工作上建立各種情感關係,包含從冷漠疏遠到在忙碌工作中產生的戀情。遠距工作在疫情期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對社交
關係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當公司的信任度較高時,所產生的催產素能讓團隊更快形成,並且更有效地共事。保羅·J·扎克在他的研究中解釋了這一點。團隊需要兩個工具才能充分發揮成員的潛力:一個是成員之間的信任,另一個則是對工作意義的理解。這兩項都有科學根據,能夠確保提升公司文化和獲得更多的利潤。
P.91
人的祖國是他一生中的前六年。
——安立奎·羅哈斯(Enrique Rojas)
P.93
最初的連結
我們出生時的環境和童年時期的陪伴者對我們的成長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正常情況下,我們的依附對象通常是父母;在其他情況之下可能是單親的母親、祖父母、叔叔、阿姨、保姆、老師等人,甚至在更複雜和困難的情況下,可能是寄養家庭。早產兒如果在出生後的最初幾週甚至幾個月內都在保溫箱裡度過,無法與母親接觸,這也會對他的情感和依附的世界產生影響。
父母和照顧者在嬰兒生命的最初幾年與他們建立的連結就是依附關係。嬰兒在無意識中感知到自己被愛和照顧的方式,以及他們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這將對他們成年後的人際關 係、個性發展、認知能力以及身心健康產生深遠影響。
如果你有興趣深入了解,我推薦你閱讀拉斐爾·格雷羅(Rafael Guerrero)的《情緒教育與依附》 (Educación emocional y apego)一書,這本書是補充此主題的絕佳讀物。
P.96
曾經的那個孩子
就如我所說的,每個成年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孩童時代的自己。你、我、每個人,我們都是人生經歷的結果,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夠適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從出生那一刻起我們就不斷在適應,這漸漸塑造了我們的個性。我們的身分認同主要在童年時期形成。衝突對你的童年產生了什麼影響?你父母之間的關係如何?在學校的經歷為何?和兄弟姊妹的關係如何?對死亡的最初概念是什麼?你是否曾感到被愛和被理解?你是否被親情包圍?是否有人曾傷害過你,並且那個傷口仍然存在?你是否記得自己的童年?朋友們對你好嗎?你是否曾感覺自己是團體的一分子?你是否曾感到被重視和有能力做事情?
P.105
創傷
童年時期遭受忽視和虐待可能會在孩童的生命中留下印記,並導致精神和情緒疾患,甚至健康問題。幼年時期的有毒壓力會長期活化皮質醇,並減緩神經元連接的正常發育,從而導致學習和行為發展的決定性失敗。透過腦部影像,我們可以看到當創傷發生時,大腦會出現一種稱為「解離」的狀態,就像是腦部的「斷電」,這是心靈和身體之間的一種分離,因為心靈意識到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的巨大痛苦。痛苦可能是一頓毆打、性侵、攻擊性的畫面、屈辱或嚴重的侮辱等。
❝為求生存,心靈會迴避真相和痛苦。❞
這種心靈的解離是一種保護機制,目的是避免感受或記錄正在發生的殘酷事實,並在創傷事件再次發生之前啟動。這是那些長期遭受頻繁性侵或虐待的人特有的系統。原因是什麼?就是不去記錄、將其遺忘並避免將這些經歷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在我的諮商中,我經常觀察到這種現象。很多時候,當我要求某人敘述一個痛苦的事件時,他們會發現自己的記憶中存在空白。
P.110 - 111
情緒基礎
童年時期發生的事件會在我們一生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大腦將這些情況視為熟悉的事(在家中所經歷的事被視為正常的事情),而這形成的基本結構區域,我稱之為大腦的「已知區域」。在這個區域我們建立了「情緒基礎」,這會影響我們成長的方式,也是在成年後,我們會將所發生的事情評判為好或壞的心靈區域。
「磚塊」(也就是大腦)和「水泥」(也就是心靈)在我們最稚嫩的年紀時在很大程度上
形塑了我們未來如何去愛和學會處理情感。讓我們想像一個人的童年時期:父親酗酒,父母之間惡言相向,成長過程中處處充斥著攻擊或咆哮,經濟困難或理財不善,或經常目睹謊言和欺騙。所有這些畫面都會在他的內心留下深刻的痕跡,對他的成長產生影響。
成年後驗證童年時期的經歷
有趣的是,隨著我們長大,我們會對所經歷過的事情產生變化。也許我們能夠療癒那個創傷,讓它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影響到我們;或者它也許仍潛伏著,在我們的個性留下深刻的烙印;或者它可能處於沉睡或無意識狀態,我們尚未學會管理和引導它,直到在某個特定時刻它就會爆發。
我們的情緒基礎總會決定我們的一切嗎?幸運地,它並非總是如此。世事並非絕對,有三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 經歷過傷痛,但尚未痊癒或克服它。
- 經歷過傷痛,已經克服並以正確的方式成長。
- 經歷過傷痛,但尚未察覺到心中仍帶有這份創傷,因此仍然受到帶來傷痛的環境或人際關係奴役,這些環境和關係在成年後繼續產生影響。
有時,心智會進行自我超越和成熟的練習,但這需要內心有所轉變;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經歷一個轉捩點,意識到一些事情,並且努力去處理、分析和接受它們——接受是多麼重要啊!——並以某種方式原諒或克服痛苦和創傷。
超過半數的人會重複某些模式,明知這是不恰當的,但內心仍然感覺與童年時期的行為模式有所聯繫,因而無法擺脫它們。長期下來,這通常導致依賴性強、有毒、痛苦或極具傷害性的關係。
P.120
如果我們在童年沒有獲得健康的愛,有時在成年後我們會試圖以不適合我們的關係來填補或掩飾那股空虛。由於不了解以健康的愛為基礎的關係是什麼樣子,因此我們會接受不恰當、有時甚至是有害的情況。
面對挑戰和做決定時,這可能引發我們對失敗的恐懼、自尊心的低落和不安全感。
這種不安全感源自心靈深處的創傷,一個無法感到父母關愛的孩子,長大後會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這會對他在建立關係時造成很大的傷害。他會尋求他人的認可,或者反過來,他會傾向於孤立自己,避免接觸人多的地方或工作,因為在那些地方他們會感到不自在。
❝在童年時期無法與依附對象建立情感連結, 將導致日後與他人的情感聯繫不足。❞
父母是依附對象的代表,負責為孩子提供穩定的情感。
P.122
為什麼我現在提出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重要且有必要了解的觀念。在人生最初的兩年中,依附的類型會成形,而在這段時間內,右腦半球居於主導地位。丹尼爾·席格(Daniel Siegel)將其稱為「共鳴」:照顧者的右腦與孩子的連接對於確立安全依附、適當的認知和情感發展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這種共鳴的關係,或如同專家所說的「心智對話」(由右腦對話到右腦),很有可能會產生不安全的依附。
P.137
從青少年到成年
許多童年時期的創傷在青少年時期開始展現出不良影響。這是一個充滿熱忱的階段,但也是尋求獨立並找到自己在世界上定位的時期。
在某種程度上,青少年時期是我們童年時接受教育、關愛與教導的結果。如果我們小時候被剝奪了情感、關愛和同理心,就會更難處理情緒,並且會產生尋求強烈感受的行為,而還有時是完全有害的。
如果青少年的依附對象是健康的,並且同時表現出關愛和明確的界限,那麼這個階段可能不一定是充滿衝突的時期。這是一個成長和內心掙扎的時期。穩固的情感支持將幫助一個人用最好的方式度過這個時期,那些具有攻擊性、憤怒或衝動行為的青少年背後,往往有一個未被教導要健康地去愛自己、表達自己和感受到被欣賞的童年。
這種憤怒,這種有時具有破壞性的行為源於自卑、個人巨大的挫折感和極度脆弱的情緒,可能導致人格障礙、廣泛性焦慮症、明顯的憂鬱傾向、對強烈情感的不斷追求,對某些物質的成癮,甚至在尋找或維持伴侶關係遇到困難。曾受虐待的孩子在某種程度上被教導愛與虐待共存,這會塑造他們成年後對愛的看法。
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深信那些愛他們的人同時也會傷害他們,亦會認為愛與傷害同時存在是正常的。然而,當這個階段出現良好的依附對象時(無論男性或女性、朋友、導師、教練、叔叔等),這些脆弱的年輕人的生命得以變得強大。尋找維他命人來治癒我們的傷口永遠不嫌晚。
P.141
不安全依附的類型
依附類型有兩種:安全依附(或者我喜歡稱之為「維他命依附」,稍後我會更詳細地論述),以及不安全依附。現在我先談談不安全依附。
當一個人屬於不安全依附類型時,這會成為未來發展情緒或心理疾病的風險因素。風險因素可以理解為吸菸與肺部疾病或癌症之間的關係。並非每個吸菸者最終都會罹患嚴重的呼吸系統疾病,但我們知道,吸菸會增加罹患此類疾病的可能性。
很多經歷不安全依附的人不知道如何表達,也不知道要與誰分享。有時,閱讀相關資訊、參加治療小組、觀看能讓自己產生共鳴的電影會有所幫助。生活中,我們學習透過觀察他人和聆聽他們的經歷來教育我們的心靈。與經歷類似的人建立聯繫,或者找到一位不帶偏
見陪伴的治療師,這樣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學習成長。不安全依附是否會演變成嚴重的疾病,這要取決於一連串的變數,這些變數值得我們特別指出。
P.144
兒童的創傷經驗會使他深受其害,但是,創傷性的依附方式是否會在成年後演變成更嚴重的心理障礙,這取決於一連串的因素:
- 發生困難情況或創傷的年齡:新生兒、五歲或青少年時期發生的困境或創傷是不同的。每個階段都不一樣,而影響也會不同。
- 是否有其他人可以在環境中提供愛和安全感,將傷害的程度減到最低。
- 創傷持續的時間。
- 孩子的基本個性。在一個有多個兄弟姊妹,甚至是雙胞胎的家庭中,經歷相同的衝突情況時,每個人的反應可能是不同的(事實上,通常不會相同),因為每個孩子的性情和韌性都不同。
擁有韌性的人在個性中有些人格支柱,幫助他們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艱難時刻堅持下去。
這些支柱當中許多是在童年時期形成的:父母所給予的安全感、健康和沒有侵略性的環境、能在困難時刻感受到支持等等。
如果孩子生活在父母之間頻繁的衝突裡,並且感受不到被愛和安全感,那麼將來會發展出更加脆弱的個性。
根據每個孩子的性格,與照顧者的互動應盡可能健康,以幫助他們充分發揮潛能。
每個人的故事都不同,父母的生活也充滿變動,這些都會影響孩子們的平衡。
如果父母設法灌輸孩子安全的依附感,這就像是一種「疫苗」,保護他們在未來不至於無法應對。另一方面,那些具有不安全依附感的人在面對有挑戰性的事件時可能會崩潰:失去工作、孩子學業失敗、醫療診斷或與朋友間的衝突。當成年人「受傷」時,一切都會變成壓力因素,這就是他們與那些具有安全依附感的人之間的差別,後者通常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應對所發生的事情。
這種不安全依附感又可以細分為:
一、焦慮/矛盾型依附
這種情況可能在家庭中發生,例如父母親其中一方離家,或者家庭關係往返不定,在父母分居或離婚時,對孩子來說是極其脆弱的時刻,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如何向孩子傳達分開的原因,以及如何與離開的父親或母親保持聯繫。要清楚地告訴孩子、不指責任何一方、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並在這個極為痛苦的時刻安撫他,以免破壞現有的安全依附關係。同樣地,如果父母在經歷一段困難時期後重修舊好,這對孩子來說可能是一個喜悅的時刻,但也可能是令人擔憂的時刻,因為他們可能害怕再次分離,對於被遺棄的恐懼被重新活化,這並不表示所有父母親離異的孩子都會發展出這種依附類型,只是不當處理這個問題可能會增加形成這種依附類型的可能性。
處於這種情感矛盾環境中的孩子,在面臨問題時並不知道父母會給予他們關愛或是冷漠以對。這將在成年後導致他們保持警戒狀態,缺乏信任且對人際關係感到不安全感。
他們在選擇伴侶和與他人相處時會感到極度焦慮,這可能表現在他們需要吸引他人的注意,如果無法做到,就會產生不穩定的行為、嫉妒心、害怕被拋棄、攻擊性的溝通和破壞性的逃避方式。
這種情況可能被描述為「既不願與你在一起,也不願失去你」。就像他們在幼年時的情況一樣,成年後他們仍然害怕被拒絕。這種依附型的成年人經常害怕伴侶不愛他們,並擔心被拋棄。這導致他們沉迷於關係中的失敗,看到了不存在的「幽靈」。
那些曾經歷焦慮性不安全依附的孩子,未來可能會發展出人格障礙。其中兩個最常見的是依賴型人格障礙和邊緣型人格障礙(BPD),。患有邊緣型人格障礙的人當中,有百分之九十二呈現出不安全依附型中的焦慮/矛盾依附型。
二、逃避型依附
據信,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表現出這種依附風格。這些成年人學會了一件事,向身邊的人表達他們的需求或情感並不會得到正面的回應或反應。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認為自己的情感和感受對於最親近的人來說並不重要,因此會壓抑和抹去內心的許多感受。他們更傾向在情感上不依賴任何人。這些人的一個特徵是,即使年紀輕輕,看起來卻很早熟:展現出獨立和成熟的形象。這種冷漠的情感有時會轉化為優越感、自傲、憤世嫉俗或苛刻。這些人很難與他人建立健康的連結,因此深受煎熬。從外表看來,他們給人一種堅強和
獨立的印象,但很多時候這只是一種保護自己的外殼,而在這個外殼底下,其實存在著深深的不安全感。這種依附風格實際上是為了避免再度受到傷害的保護機制。他們在處理自己的情感或表達情緒時經常遇到問題。他們通常是情感障礙者:難以啟齒或分享自己的情感世界。因此,當有人接近他們或試圖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時,他們不知道如何應對,並為此而感到痛苦。
他們很難真實地展現自己,反而更傾向控制所表達的內容,理性多於感性。有時他們對待他人會像遵循手冊一樣,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感受行事。在愛因斯沃斯的實驗中,關鍵在於當母親離開房間時,這些孩子表現得無動於衷,且母親回來時也不表現出喜悅,他們甚至避免接近父母,但始終不表露情感。我們必須知道,
當父母離開時,他們的內心正在軀體化(出現了皮膚電導、心搏過速和皮質醇水平升高等反
應)。
三、混亂型依附
依附的兩個支柱是自主性和連結,兩者之間必須有良好的平衡。
在焦慮/矛盾型依附中,連結占主導地位;
在逃避型依附中則存在較高的自主性。
此依附類型是焦慮/矛盾型和逃避型的混合體。 孩子會表現出矛盾的行為,有爆發性的行為傾向,並且難以與照顧者相處。這種依附風 格也被歸因於他們在嬰兒時期發送的信號得不到照顧者適當的回應。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確 定對他們身邊的照顧者能抱有什麼期望。
當這種類型的孩子長大成年後,他們可能重複在童年時期看到的模式,行為從具有攻擊 性轉變為討人喜歡或控制欲強,這些人的內心感到極度挫折和憤怒,儘管內心最渴望的是建 立親密關係,卻反而常常拒絕建立關係。他們自己也承認不理解自己內心所發生的事情。許 多時候,他們可能意識到自己感到迷失、無所適從或空虛。這些人在成長過程中缺乏自我認 同模式,對於建立或維持關係毫無依據。有時候他們可能有衝動的問題,甚至可能需要藥物 治療來緩解情緒的波動、憤怒和挫折。
近年來,反社會性格已經受到廣泛研究。密西根州立大學的亞歷山德拉·伯特 (Alexandra Burt)最近對雙胞胎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以身體攻擊或專制嚴厲的方式為基 礎的教養會促使這些孩子在長大後表現出反社會行為。
P.162
情緒管理取決於什麼?
情緒管理意味著在面對壓力、憤怒、悲傷或挫折時能夠調節自己的情緒。正如同我們已 經看到的,這種管理的學習始於童年時期,為了能夠健康地啟動它,初生幼兒時期就必須有 一位照顧者能夠正確且均衡地滿足孩子的需求和問題。
我們與他人建立連結的方式,與我們在童年時期受到的照顧和學會愛的方式密切相 關。我們如何被愛,就學會如何去愛。你被愛的方式,就是你愛人的方式。 當童年時期出現創傷,成年後的情緒管理能力就會受到損害。這些創傷可能程度各 異————兒童屢次被忽視、虐待、霸凌、騷擾、侮辱等等——————但即使是中度或輕微的創傷也會 留下痕跡,情緒上的傷痛會影響你成年後的自我。了解你的具體情況,將使你能夠踏上康復 之路,治癒曾受過的打擊,
P.174
七·我如何解讀事情?
我曾多次重申,幸福不是我們所經歷的事 情,而是我們如何解讀它。這種解讀取決於三個 因素:信念系統(我們對生活的想法和期望)、 情緒狀態,以及我們過濾訊息並保留重要內容的 能力(上行網狀活化系統)。最近,我添加了一 個圖表,我認為它能更有用地理解每個人對於所 發生的事情的解釋,我稱它為「從感知到行動」 圖表。我通常會把此圖表簡單畫在紙上,用一隻 大眼睛和一顆心來表示。
我們都能感知到周圍環境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透過眼睛),這會對情感層面產生影響(也就是 心),在這之後,我們或多或少會思考,然後採取行動(如果無法行動,我們就會陷入僵局)。
P.176
內在聲音反映我們面對生活中不同挑戰、計劃或目標的態度,它應該成為支持我們的力 量,而非將我們拖入泥淖,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自我阻撓,否則我們在開始做事之前就先失敗 了,對於浪漫約會、醫學檢查或考試之前的態度,都會對最終結果有顯著的影響。 最近,我很訝異有很多人向我諮詢這個問題,「當內在聲音指責自己時,我該怎麼辦?」、「要如何處理批評自己的內在聲音?」、「為什麼我對自己如此苛刻?」,有時我還 會聽到這樣的話:「我變胖了」、「我的老闆不重視我」、「丈夫對我冷淡」、「沒有人注意 到我」、「沒有人重視我」、「我永遠不會有孩子」等等。在《親愛的,那不是你的錯》一書 中,我曾深入探討這個問題,特別是因為這對我們的健康和生活中的目標有著重大影響。
現在,我想分享這個聲音的另一個面向: 它的源頭來自哪裡?
要教育內在的聲音是一件複雜的事,但成功做到這一點,將使我們更接近於與自己和平 相處,並在個人和職業生涯中展現出最好的一面,這個聲音對於工作的影響非常大。據我所 知,內在聲音總是一直在責備自己的人,很少能在職場上取得成功,當然,我指的不是自戀 狂(他們只會聽到讚美和誇獎他們所做一切的聲音),而是那些內心善待自己,不自責,並 且踏實地生活的人。
內在聲音從何而來?
這些年我一直在尋找一個最能解釋這個概念的比喻。我設計了一個圖表,希望對你有所 幫助,你可以將圖表內容應用在你的生活中。
❝童年時期的錄音機,成年後變成了內在的聲音。❞
每個人出生時都帶著一部空白的錄音機,就像是一張白紙或空無一物的硬碟,其中記錄 著我們所經歷的事件、感情和對話。內在聲音的關鍵在於:
- 我們的父母是如何與我們溝通的。例如「我不為你感到驕傲」、「你是個懶惰的孩 子」、「你真是個好兒子」、「你真是一團糟」,或者「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做到」。
- 父母之間如何相處。例如:「沒人能忍受你」、「我非常愛你」、「你真是個麻煩的人」、「你很自私」等等。
- 父母如何在別人面前談論我們,例如:「這孩子真讓人難以忍受」、「他真是個討厭 的傢伙」、「我兒子是個非常棒的孩子」等等。
「父母」這個詞,你可以替換為兄弟姊妹、老師或親近的親戚。父母親是最有影響力的 人,但我們也可能透過學校、祖父母、兄弟姊妹或朋友等其他關係來削弱這個內在聲音。
影響有多大?
這並不是精確的數字,但對於試圖理解自己過去的成年人,或是擁有孩子並希望幫助他 們 展現最好一面的父母來說,這可以作為一個指南。
這種影響力在六歲前特別重要(約占百分之五十);從六歲到十二歲,重要性占百分之二十五;而在之後的人生中占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這些數字只是大概的估算,並不是確切 ,但我認為它們反映了每個階段的重要性。
的 一個人可能在與父母親的關係中擁有安全和健康的依附,但也可能碰巧遇到一段可怕且 具侵略性的戀愛關係,或是與棘手的老闆打交道,這些都會造成創傷並影響態度、恐懼和內 心的聲音。但如果童年時期相對美好,療癒這些創傷將會更加容易。
對此鮑里斯·西呂爾尼克給出了一個精闢的解釋:成年人的安全感來自於童年時期建立的依附系統。當創傷發生在 擁有健康和安全依附的人身上,以及發生在擁有破壞性和侵略性依附的人身上,兩者相較之 下,創傷帶來的傷害程度並不相同。
這個聲音某種程度上影響我們的自尊,並在很多時刻產生猶豫不決的問題。生活本身變 得複雜,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哪個決定是正確的。做出選擇即表示對事物或多或少有清晰的 想法,在做決定、做選擇和行動時有堅實的支柱。為此,我們需要了解自己是誰,知道自己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了解自己的極限,以及在生活中願意放棄些什麼。
❝自卑的人會有一個內在聲音在不停地責備他們。❞
P.210-211
愛情演算法
去年我讀了法國記者茱蒂絲·杜波塔(Judith Duportail)的一本書《愛情演算法》 (L’Amour sous algorithme),在那之前我在《衛報》(The Guardian)上讀過她的一篇文 章,標題是《我向Tinder索取我的個人資料,他們給了我八百頁的深藏祕密》。這本書講述 了她如何沉迷於這個應用程式,以了解它的運作方式,並探討Tinder與自尊和焦慮的關係。
多年前,我在單身時參加了一位好友的婚禮。在舞會上,新娘的母親走近我,告訴我不 要擔心,愛情很快會來臨。我認為這樣的觀念對我造成很大的傷害。找不到人生伴侶似乎被 判定為孤獨和挫敗。我誠心相信,我們都是為了愛與被愛而存在的,但在這個充滿激情(無 論是好是壞)和數位化的二十一世紀,找到穩定的伴侶並沒有那麼簡單。媒體給我們帶來的 壓力、無法停下來珍惜現實生活、許多膚淺的關係,以及對社交媒體的絕對依賴,這些都使 我們陷入一個巨大的空虛中。渴望被愛是合理的,但學會在沒有伴侶的情況下快樂生活是一 項重要的任務,這可以讓我們在未來發現生活中其他美妙之處。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從事 志願服務、旅行和體驗文化,這會充實我們的心靈和思想!
P.216
同儕壓力
曾經有個男生告訴我,他加入Tinder是為了找一個女孩上床,這樣他就不再是朋友圈 裡唯一的處男。小心這些從未有過性經驗的人,他們會因為覺得自己被看不起而給自己施加 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謹慎行事。因為為了取悅別人而強迫自己,意味著我們在為了 別人的看法而行動,而這從來就不是最好的動機。
以消極方式經歷第一次性經驗的人,將來可能會發展出不安全感和焦慮。我曾多次在
諮商中看到我們所稱的心理性功能障礙是不良的經歷引起的—————包括陽痿、早洩或陰道痙攣
等。男性受到壓力,如果沒達到自己設定的目標,可能會感到羞愧,並影響他們的自尊心。
康乃爾大學的莎朗·賽斯勒(Sharon Sassler)博士進行了一項研究,調查了六百對情 侶的性關係起始時間。數據顯示,其中三分之一的情侶在交往的第一個月就開始了性生活。 結果顯示,那些在第一次約會或頭幾週就開始性關係的情侶,在長期的感情關係中品質較 低,分手率也較高,研究還指出,對許多女性來說,早期的性行為被視為承諾的象徵,而男 性則有不同的理解。
P.220-221
我堅信我們必須在生活中各個方面促進適當且平衡的文化,而其中當然包括健康的性教 育,我們必須避免引入有害的概念和扭曲的影像,並且應該對數位媒體中的性內容,特別是
具有攻擊性的內容加以規範,解釋和宣揚性的好處,同時警示色情片帶來的有害影響,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社會,讓色情片不再成為眾人的消費品,這將有助於恢復許多伴侶關
係的健康,因為在世界上許多地方,色情片已經成為伴侶分開的原因,在美國,近乎一半的 離婚是因為色情片導致的。別忘了,它提供一個不真實、充滿幻想和烏托邦式的性愛形象。 年輕人因此受騙,認為自己會感受、體驗與經歷與螢幕上所看到的類似過程。看過色情片 後,控制我們反思能力和抑制衝動的前額葉皮質會受損並弱化。我們會變得更加原始,更容 易用本能行動,並對異性產生一種危險的傾向,這種傾向將對象過於簡單化和物化,從而使 我們疏遠現實生活中原本親近的人。
色情片扭曲了現實,讓觀看者相信現實生活中極不可能發生的情況。它傳達了女性總是 渴望性愛,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女性等同於狂野性愛的這種觀念,它混淆了觀眾的視聽,讓他
們不知道女性的運作方式、性興奮的時間和女性實際喜歡的事物。
P.230-231
根據大腦迴路區分的愛情
海倫·費雪在愛情的問題上,從科學的角度區分出三種不同類型的愛情,每一種都與不 同的大腦迴路相關,她提到了:
一、性慾
這是最生理和衝動的迴路,身體會在這裡尋找各種不同的伴侶。
二、浪漫愛情
在這裡,你的心智只允許你專注於一個人。你會產生占有慾————他/她是我的—————你也 會變得偏執,頭腦無法停止思考那個人。
三、依附
這種大腦迴路是原始的,會產生多巴胺,活化快樂和成癮的荷爾蒙————伏隔核。這是我 們在詩歌、歌曲和電影中熟悉的愛情。這種戀愛讓你覺得你所認識的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 沒有人能與之相比,你是個幸運兒,因為你找到了真愛。
海倫,費雪將這個階段描述為你決定與伴侶在一起照顧孩子的階段,我稱之為穩固的伴 侶,這是熱情稍稍減退的時刻,但是親情與日俱增。你們學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共同生活,努力創造一個友善、有價值觀和情感的家庭。
很多人在這個階段感到驚慌,因為他們不再有相同的感覺。確實,從生化角度看來,多 巴胺的水平會降低。這是催產素分泌的時刻,是安頓、成長和鞏固已建立的家庭時刻。
P.231
當我們墜入愛河時,大腦會產生什麼變化?
當我們墜入愛河時,一切都變得與眾不同。周遭的事物變得更美好了,世界也變得更友 善,歌曲會讓我們想起那個特別的人。我們想跳躍、跳舞,整天笑臉迎人。談戀愛時,我們 的身體會產生腦內啡,對痛苦和悲傷的感知程度會減輕,任何時刻都是值得享受的。我們的 食慾下降,睡眠時間減少,但我們都能忍受。我們的情緒比平常更加強烈,微小的刺激也能 引發喜悅。
每個人在生活中對愛的感受都是不同的。
當我們墜入愛河時,有四種荷爾蒙會變得活躍:
一、催產素
它負責增加想要擁抱和觸摸對方的渴望,它也幫助我們無條件地信任對方,想像未來共 度一生。而且不僅如此,它還強化了連結和愛意。
二、腎上腺素
它負責引起心搏過速、胃部攣縮並降低食慾,這會讓我們專注於對方,也就是眾所周知 的「眼裡只有他/她」。
三、多巴胺
它是令人愉悅的荷爾蒙,負責獎勵迴路,並與成癮有關。在談戀愛時,特別是在激烈地 墜入愛河時,體內會大量釋放多巴胺。這就是為什麼在戀愛的階段,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地想 要感受並見到那個人,重複這種愉悅的體驗。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會沉迷於與對方親近的感覺。多巴胺有助於 記住那些最初時刻最微小的細節。
四、血清素
它是幸福的荷爾蒙,與食慾、旺盛的性慾以及無窮能量和享受的感覺密切相關。
P.234
真正的愛出現在熱戀消失後,這時我們會意識到這段關係是否有未來。這些時刻非常重 要,因為我們會注意到對方是否想為正逐漸穩固的關係而奮鬥。我們都希望找到一個這樣想 的伴侶:「我會竭盡所能來維護我們之間的感情,如果感情變淡了,我會努力挽回它。」相 較之下,在內心深處,沒有人願意和這樣的人在一起:「只要感覺還在,我就會愛你和關心 你;但一旦關係變得緊張了,我們就分手吧。」這樣的人會讓人感到非常不安!
❝愛情不僅需要激情和強烈的情感,還需要穩定感和平靜。❞
P.238
一、火花
有一種火花在你的心中萌生,你想更進一步了解那個人。你喜歡他/她的肢體語言、 他/她的眼神、微笑和身材,還有他/她的談吐和風格。他/她身上的某樣東西驅使著你想 要多與對方相處,對
二、理智
這裡涉及到智慧。是的,如果在第一次約會或在初期階段就宣布永遠的愛、展示所有底牌或發生性關係,那麼這段關係可能無法持久。我不是說在這些情況下的關係一定會告吹, 但失敗的機率可能要高得多。你的頭腦會變得混亂,不知道這個人是否真的適合你。 不要忘記,我們通常不會因為第一次約會的熱情、身體上的吸引和強烈情感的驅使下 進入戀愛關係。在這些情感激昂的時刻很難讓人冷靜地思考。在大腦的前額葉皮質處於關閉 狀態時,你很難辨別、分析和冷靜做出決定。擁有主宰自己決定的能力(我指的不是取消感情,而是引導感情)是在最初的熱情或火花出現後取得成功的有力關鍵,你需要運用理智。
在我的演講和諮商中,或對我親近的人,我經常解釋理想的做法是問自己以下幾個問題:
- 對方是否適合我?
- 對方是否讓我成為更好的人?
- 對方是否符合我一直以來認為適合我的性格和人生觀?
- 對方是否符合我的標準?
最後一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將在接下來的內容中詳細解釋。前三個問題的答案必須是肯定的。
如果在思考這些問題時發現自己不確定,或者明顯看到了一些不適合自己的地方,那麼最好不要繼續前進,這可能有各種原因:對方已婚、有子女、居住在他國、是會讓我們痛 苦的人、已經訂婚、吸毒、風流、不想認真交往等等。 沒有比愛上錯誤的人更糟糕的事情了。如果我們理智上明知道不適合卻仍然堅持下 去,情感上的傷害必然會發生,無論是以下哪種情況:最終鼓起勇氣結束關係後,它在我們 心中留下痕跡,兩人都會因分手而痛苦;或者在面對未來的差異中,生活的衝突會使這段關 係破裂。
三、墜入愛河
這裡涉及真正的愛,浪漫而純粹的愛。墜入愛河是一種渴望和吸引融合在一起的感
沒有比愛上錯誤的人更糟糕的事情了。如果我們理智上明知道不適合谷 去,情感上的傷害必然會發生,無論是以下哪種情況:最終鼓起勇氣結束關係後,它在我們 心中留下痕跡,兩人都會因分手而痛苦;或者在面對未來的差異中,生活的衝突會使這段關係破裂。 在一段關係中產生的感情有時會深厚到即使明知道對方不合適,我們仍然正式確立了關 係,但卻不知道如何終結。金字塔的關鍵在於這一步,我會在下一章中解釋。覺,希望這種感覺永遠不會減少或消失。
有許多伴侶開始交往是因為他們認為彼此適合——————「他/她適合我而且對我很好」。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強烈的激情或深刻的愛,但有足夠多的因素讓他們繼續下去————「他/她很有價值」、「他/她很照顧我並且很有吸引力」、「我的父母喜歡他/她」、「他/她的家人 都很棒」、「他/她是個在各方面都很出色的人」。
四、意志
如果選擇是正確的,意志將成為你餘生的偉大盟友。愛不僅僅是一種感覺,更是一種 意志的行為。我決定努力經營這段關係,因為它適合我,因為它對我來說是合適的、對我來 說是好的,並且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即使有時會受苦也不放棄,我不能只將愛建立在感情或理由的基礎上,因為根據定義,這些都是會波動的,會不斷變化和發展。有些日子心情 好,有些日子情緒低落,因此我需要使意志發揮重要作用。誰不曾遇過這種情況,明明是你 的朋友,但有時候你卻受不了他,感覺被他糾纏?誰不曾有過被父母親或孩子壓垮的感覺? 感情因多種因素而變化,它們需要正確引導;但意志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
在愛情中,意志代表著用心照顧細微之處,記得重要的日子,以及待人的方式等等。日 常瑣事從來都不是無足輕重的,相反地,它是生活的支柱,也是讓伴侶快樂的基石。意志涉 及努力,問問自己如何能讓對方快樂,對方面對困擾時,有什麼是我能做的,好減輕他/她 受的苦?如果你對待對方的方式是好的————即使面對逆境、疲憊或例行公事———————你們在一起的生活將變得與眾不同。
P.274
❝高敏感人身上擁有超越常人的能力, 能夠感知外界刺激與正在發生的事件並因此產生感覺。❞
特質及特點
能夠感知外界刺激與正在發生的事件並
高敏感人的主要特質和特點包括:
- 善於觀察,他們能強烈感知各種刺激(噪音、味道、顏色、氣味、評論、表情等)。 事實上,根據一些研究,他們傾向於以不同的方式處理感官感知到的刺激。
- 他們的感覺更為強烈。 ·喜歡談論情感,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有些男性在談論自己的情感時會感到尷尬和不被理解。
- 他們更容易感到稜邊,也更容易被過多的刺激淹沒。
- 具有對接收到的資訊深入思考的能力。 在面對情況或挑戰之前,他們往往會更加謹慎小心。
- 處理訊息非常細膩,
- 可能會表現出某些強迫症特徵。
- 對被批評和被拒絕更加敏感。
- 更具有同理心,
- 挫折會使他們感到更加痛苦。
- 喜歡幫助他人,傾向於支持別人。
- 需要短暫的獨處時刻。
P.278-279
高敏感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如果你是高敏感人,那麼與伴侶之間的小事就可能讓你極度痛苦。也許你會感到沮 喪,因為對方不像你那樣強烈地感知事物,或者不理解你的情緒、悲傷時刻和沉默,當你需 要對方更用心地傾聽你時,對方卻顯得不夠感同身受,這也許會令你感到痛苦。 如果一個高敏感人不知如何管控自己的細膩敏感和善加表達自己,那麼他就可能會在關 係中感到非常脆弱。能夠談論這一點並共同探討這個主題可能會很有幫助。在諮商中,我經 常與高敏感人的伴侶見面,向他們解釋這種人的細微差別以及他們的感受和行為方式。
我想說明一點:
如果我們學會好好處理高敏感的特質,它會是一種天賦,一份禮物與一項巨大的優點。為此,高敏感人需要:
- 理解他人的感知和感受與你不同,你不能要求別人有和你一樣的敏感度和關注度。
你的伴侶不太可能達到和你相同的敏感度,即使有,也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 理解自己如何處理資訊、刺激、情緒和痛苦。
- 了解自己擁有更多同理心的能力,因此更容易和更有能力幫助他人。
如果你認同這些觀點,或者認識身邊有這樣的人;
- 給這種感受取個名字。許多我認識的人在理解自己是高敏感人時都鬆了一口氣。
- 學會管理你的情緒,試著辨識出使你處於警戒狀態的主要壓力源。
- 計劃一些任務來幫助你引導高敏感特質:寫作、散步、閱讀經典文學、演奏樂器、 縫紉、背誦詩歌、按摩、接觸大自然、繪畫、休息、從事運動等等。
- 設立界限。根據定義,高敏感人通常設立較少的界限,這是他們感到壓力和疲憊的 原因。由於感受太多,當他們全心全意地投入時,會承受更多痛苦。在這些情況 下,說「不」反而是有益心理健康的,也會幫助你自我感覺更好。高敏感人在情感 層面上的自我照顧不周是很常見的,有時需要教導他們設立界限。
p.281
有些人無論走到哪裡都帶來幸福,
而有些人則是在離開後才讓人快樂。
——奧斯卡·王爾德
p.283 - 285
雖然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但不同的人對我們的影響並不是中性的。有些人際關係適合我 們,有些則不然,有些人會為我們帶來平靜和快樂,有些人則讓我們感到疲憊和煩躁。請盡 可能選擇我們周圍的人,並與他們建立健康的關係,這將影響我們的心理和情緒健康。
❝一個人本身並不是有毒的,有毒的是他對你產生的影響。❞
當我們難以離開對我們有害的人時,就會出現另一個問題,這就好像我們對某些人產生了依賴感,而這些人對我們來說並不總是帶給我們最好的影響。
另一方面,有時我們必須誠實面對自己:問題是來自於我們自己,而不是他人。有些對有毒環境敏感的人,其實是自己出了問題。有些人對於自己遭到拒絕的情況極為敏感,誤以為他們周圍的人是有毒的,而實際上的問題出在他們對現實的感知。在接下來的內容當中,我將試圖闡述所有可能性。在你生命中的某個時刻,你可能會發
現自己與其中某些情況相符。
本章的職責有三項:
- 首先,分析我們的人際關係,看看是否有任何有毒成分的人,並盡量妥善處理關係:
- 其次,我們必須避免對他人產生有毒的影響(是否犯了使他人產生排斥感的行為?),
- 最後,讓我們成為一部分的解方,而不是成為問題本身,讓我們立志成為身邊人們的維他命人吧。
我想再次強調,這裡使用「有毒的人」一詞,是指會使人皮質醇中毒的人。
有毒的人使我們自動產生排斥和不適,不論是否有依據,他們的存在都會讓我們感到不安,有束縛感,令我們備感壓力,並使我們感覺失去了自由。有毒的人通常具有侵略性和攻擊性;他們侵犯我們的空間和對話,武斷地評判我們的生活和觀點。然而,也有些人僅僅透過肢體表達、尖酸刻薄的言論和偶爾的諷刺就能讓人感到不適。最後一類人更難分析,因為他們的態度和動機聰明而微妙,他們所施加的負面影響通常是出於某種需要揭示的原因,在所有情況下,與這樣的人共處都令人筋疲力盡,當這些人在人生道路上與我們擦肩而過時,我們會感到非常惱火。
有毒的人對身心有什麼影響?
正如我已解釋過的,警戒狀態會在幾分鐘內改變我們的身體。當我們為某事擔心、感覺受到威脅或拒絕時,警戒系統會被啟動,分泌出兩種荷爾蒙:腎上腺素和皮質醇,它們是幫助我們靠著「戰鬥或逃跑」來應對這種挑戰的物質。
P.287
有毒的人就是那些與他們相處起來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的人。即使在他們離開後,我們仍然感到煩躁、悲傷和空虛。當我們長時間與他們共處時,由於他們會啟動我們的警戒系統,我們的身體會感到疼痛,因為我們的皮質醇水平上升了!
❝當我們與有毒的人在一起時,我們不會放鬆和平靜, 而是感到緊張和不斷處於警戒狀態,而這會導致疲憊感。❞
P.291
❝認識自己理解自己→接受/處理情況+原諒❞
「普遍有毒者」及「個人有毒者」
我稱之為「普遍有毒者」的人,是那些因為他們的存在而影響到許多人的人。這不是一個我特別喜歡的詞語,但它貼切地描述了我所指的情況。「個人有毒者」則是那些只會讓你感到不安的人;然而,對你周圍的人來說,他們可能並不會引起類似的不適。
舉個例子:想像一下你的上司對你而言是有毒的人,因為他困擾著你、讓你感到不安,但與此同時,整個團隊都覺得與他相處愉快,並且與他建立良好的關係。
有些人因為他們複雜的個性造成許多人的困擾,但有些人因為某些特殊原因只讓你感到煩躁,仔細分析這種情況,進而更準確地處理它,這是非常有趣的。
P.293 - 299
「普遍有毒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徵,這些特徵能幫助我們識別他們,並避免成為其中之一。這些人通常自私、消極、好嫉妒、自憐、悲觀、愛批評、愛操縱別人、具依賴性且戲劇化等等,讓我們來分析其中一些特徵。
自私者
我稱他們為「魔鏡魔鏡」,他們的生活自始至終只專注在自己身上,我如何、對我如何、跟我又如何云云,他們只會做他們想做的事情。他們需要在每一次的談話中成為焦點,他們很難表現出同理心、理解他人的處境,或察覺周遭的問題。他們不聽別人的問題,因為對別人的困境不感興趣,與自私者相處可能會讓你感到筋疲力竭,因為他們內心深處渴望你提醒他們,他們才是你應該注意的焦點。他們希望成為你生活、用餐、聚會和談話的主角。
負能量者
這些人一天到晚抱怨,在他們眼中,杯子裡有一半是空的。他們對周遭有著戲劇性和悲觀的看法,他們的上行網狀活化系統(ARAS)處於負面狀態,濾除了讓他們享受生活和感知美好事物的可能。他們對任何人事物都感到生氣,包括對你、溫度、食物、交通、政府,甚至對整個世界都感到憤怒。他們很難接受好消息或是進展順利的事情。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人,請離開並保持距離,因為你可能會經常遭受無妄的攻擊,這會讓你心煩意亂。他們把自己的問題歸咎於你,並且見不得別人好;重點是這會激怒他們,並透過壞脾氣表達出來。如果你靠近他們,你會感覺不舒服,沒安全感和焦慮。
嫉妒者
這是許多毒性人格的一個常見特徵。當別人過得很好時,他們感到苦惱,因此需要批評和貶低別人,這是蔑視、辱罵和羞辱的根源。
這些人通常懷有不安全感,他們用這種嫉妒的態度來掩蓋。這就是他們不會為他人的成就感到高興的原因。作為一種「防禦措施」,當我們和這些人在一起時,我們常常無意識地隱藏我們的成功,以避免引起對方的反感。
受害者
他們凡事都有藉口。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故事充滿戲劇性,在所有發生的事情裡都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因此,他們在他人身上營造出了內疚感,並且善於利用:他們濫用你的時間和善意,利用任何情況以求少付費、獲得好處或獲贈東西。這還伴隨著一個特別讓人困擾的特質:當你真正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卻不在你身邊。他們傾向將自己的挫折歸咎於他人,長遠來看,這最終會導致他人的自尊問題。
憤世嫉俗者
憤世嫉俗的人會使你失去活力,想被你內心的光芒,他們的陰暗情緒在幾分鐘之內就能占據你的心靈,當你靠近他們的時候,你會被他們身上的悲傷氣息感染。他們許多人是需要幫助的,因為他們正在經歷憂鬱的過程,或者需要細心照料生命中的嚴重傷口。憤世嫉俗的性格會自我反饋,由於他們沒有吸引力,因此會逐漸孤立自己,身邊的朋友也會越來越少,而那些留在他們身邊的人最終會因為忍受他們而在心理上承受巨大代價。
評論者
這些人總是有話要說,無論是你的生活,你的感情關係,你對孩子的教養方式,你的外表或你的工作,他們都要評論,無論你做什麼,他們都覺得有責任向你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通常毫不保留,近乎粗魯,這讓你很受傷,因為你覺得這是一種攻擊和直接侵犯。
你總是有種被斥責的感覺,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與父母的關係中,他們「教育」的關鍵
時刻已經過去了,但仍保留著「教育」的習慣。每個人都有缺點,缺點被別人指正(即使是以友善的方式糾正)會產生不適感,在不傷害對方的情況下,糾正別人的錯誤是非常困難的,需要用非常委婉和細膩的方式,這些人經常責備和分析我們的行為,我們應該注意這種態度是否在一段關係中開始出現,因為感覺受到不斷的批評和審視會引發一種對生存非常危險的影響,啟動人體內的警成狀態,讓我們無法休息和享受生活。
批評者
我們都認識這樣的人。當你見到他、在他身邊或打電話給他時,他總會說別人的壞話。他的生活就像一個「老大哥」在觀察別人的生活,不知疲倦地關注著別人的失敗和錯誤。
當我們接近批評者時,我們的警報系統會超速運轉,皮質醇和其他身體反應會讓我們感到壓力,而這種壓力會耗損我們的精力。如果你是這樣的人,要小心了!當你對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滿意時,你會覺得不安全或空虛,很可能就會進入輕易批評他人的世界。我通常會解釋,有一種內在的批評,是我們每次在生活中遇到或接觸某人時,腦海中會出現的聲音。接著是外在的批評,這是我們與他人分享的批評,內在批評對身體會產生相當有害的影響,因為我們對自己說話的方式會直接影響我們的健康,而外在批評,即我們向他人傳遞的批評,則具有雙重有害的效應:不僅傷害了自己,還同時毒害了環境和影響身邊人們的生理平衡,有些人認為藉著批評,我們能跟他人取得連結,因為我們在分享共同的看法,而這會產生憤怒或嫉妒性質的對話,或產生引發大笑的流言蜚語,但注意了,「有趣」和「有毒」之間的界線是非常細微的。
操縱者
這些人對你具有影響力和控制力。可能是你的伴侶、父親或母親、老闆或朋友。他們通常具有超強的記憶力,會保留資訊和數據,以便在需要時用來攻擊你,或讓你按照他們的要求行事。
只要你沒有意識到自己受到操縱,你就不會真正受到傷害。但一旦你發現自己一直以來都被操縱了,而且屢次發生,你會感到被背叛,覺得自己渺小和脆弱,這會嚴重影響你的自尊和自信心。
依賴者
這些人感覺自己極度需要另一個人,以至於最終會奴役對方,並剝奪他們自己的個人空間和自由,顯然一種情況是因為客觀因素而無法自立的依賴者(但這不是我們現在討論的情),另一種則是透過病態行為強力導致依賴他人的情況。
況他們控制你的一切行為,不斷假裝自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無法忍受你和他們的生活是分開而獨立的,這導致了巨大的精神消耗和強烈的受困感。為了阻止你脫離他們,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利用情緒勒索,意識到這一點將有助於你健康地應對這種情況。
「讓你的生活充滿戲劇性」者
幾年前我在比利時的一個電視頻道上看到一段令人驚嘆的廣告。在一個平淡無奇的村莊裡,人們在廣場中央安裝了一個紅色按鈕,上面寫著:「按下按鈕,增加戲劇性」。當人們按下按鈕時,各種戲劇性的事情在短時間內就發生了。幾分鐘過後,小村莊的生活又恢復平靜。我有時在治療中用這個廣告來向我的許多病人解釋這個概念,我稱之為「讓你的生活充滿戲劇性的人」。這些人不斷尋找衝突,如果找不到就編造出來,並樂此不疲。他們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對於戲劇性或甚至悲劇性的情況上癮。與這樣的人共處就像走進一片地雷區。
P.307 - 310
這並非易事。與有毒的人頻繁接觸會造成受害人很大的耗損,如果不能適當地處理,可能會導致身體和(或)心理疾病。對此並不存在單一的解決方法,而是根據每個具體個案的條件及其關係類型,去優先考慮或加強我提出的某些解決方案。
一、謹慎的價值
由於其中一些人的特質和個性使然,他們可能會利用對你的了解,在某個時刻以某種方式傷害你。
在社交媒體說話和發布內容都應謹慎,因為有些人會仔細觀察你的一切,以蒐集有關你生活的資訊。
二,避免接觸互動
遠離那些讓你心煩意亂的人。保持距離,並強化內心讓自己壯大,這樣你才能以最好的方式處理關係。
如果你不得不與他們打交道,因為他們是你親近圈子(家庭或工作)的一員,試著在和他們相處之前做好心理準備,這樣會減少受害的程度。這並非自私的行為,也不是軟弱或怯情的表現;這是自我保護。在這些情況下你需要保持距離。
三,忽視對方的意見
我們已經談到大部分的有毒影響來自於他們對你的生活持續或惡意發表評論,這使你疲憊不堪。如果你能忽視他們,你會更不受他們的言語和行為的束縛。將他們的言論以及他們說話的方式相對化。學會使用「心理雨衣」,,讓評論和目光從你身上滑落。提醒自己,這些傷人的評論來自於那些你已經知道需要小心應付的人。
四,別讓他人對你的健康擁有太大的掌控力
你已經知道這會對你的心理和身體產生什麼影響。你想因為這個人而感到煩躁嗎?你是否意識到,如果你允許這件事發生,那麼你的身體將產生一連串非常負面的生理後果,例如皮質醇中毒或炎症?
如果你了解這種影響,你將會更清楚後果,也就能更好地面對這種情況。這將賦予你應
對的內在力量。
五、學習適應
有些人出於我們難以理解的原因,必定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無法總是避開他們,如果是這種情況,而你又無法遠離他們,那麼請你做一個適應的練習。首先,需要分析對方是「普遍有毒者」還是「個人有毒者」。探究這個人對你造成問題的根源,並試著理解為什麼你會如此煩躁。當你看到他時,你有什麼感受?你感到不安嗎?你有沒有察覺到他在評判你?你是否有憤怒、恐懼或氣忿的感受?請試著成為自己的心理治療師,逐步進行診斷。
六,理解其行為
我要再次強調,理解會帶來解脫,如果你試著辨別對方行為背後的原因、問題和困難,你將更能理解他對你做出的行為,你的皮質醇也會減少上升。你面前的這個人有什麼問題?他有什麼故事?他是因為害羞還是缺乏安全感?他有自尊心的問題嗎?沒有人教過他如何去愛嗎?他是具有攻擊性的嗎?你是他的宣洩對象嗎?他嫉妒你嗎?他只對你有這樣的反應嗎?換句話說,當你理解這個有毒的人時,你會感到解脫,有時你需要停下來仔細分析,無論是你的母親、老闆、前夫或是孩子,他正在經歷哪個重要階段?
為了讓感覺良好,你就必須了解他的生平,為此有時需要傾聽、理解、深入、提出問題等等,而這正是我們不想對這類人做的事情。
七、用心感受
用心對待傷害你的人是多麼困難啊!我並不是說你要被他們擊垮或被他們利用,我指的是避免用太嚴厲的眼光去評斷他。冷漠和憤怒是一種毒藥,會占據你的內心・如果你發現這樣做讓你感到寬慰,那就嘗試去理解,你將在個人成長方面取得很大的進步。相反地,如果你感覺到他們濫用你的善心,那麼請遠離他們,保護自己。接近這樣的人對你沒有好處。
八、寬恕
寬恕是一種愛的行為,它會帶你回到過去並安然無恙地歸來。這是多麼困難,但同時又多麼重要的一件事!這並不容易,需要成熟、時間和謙遜。它是一條緩慢而漸進的內心解放之路,如果一個人不原諒,他就會固守在過去的陰影中,變成一個懷恨在心的人,無法去
我不認識任何一個對身邊的人懷有仇恨而又幸福的人,因為仇恨是一種毒藥,會使身心
中毒,有時,原諒意味著與那些傷害你的人保持距離。這並非指「我看到你時無動於衷」,因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是一種理想化的想法,而是指「我知道我需要與這個人保持距離,才能以更客觀的角度看待他,這樣在看到或想到這個人時,就不會受到如此深的影響」。
P.334
如何辨識維他命人?
- 他們會提升你的自尊心。
- 他們會支持你、激勵你。
- 他們會激發你最好的一面。
- 他們會試圖舒緩痛苦的時刻。
- 他們希望理解你而不評判你。
- 他們會傳遞歡樂和熱情。
- 他們懂得感恩並傳遞感激之情。
- 他們會幫助你擺脫負面情緒並 強化正面情緒。
- 他們具有幽默感。